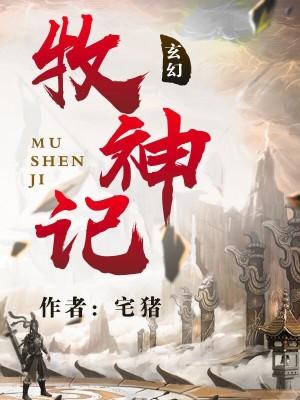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我正在把自己修改成最终妖魔 > 256尊主红盖头(第2页)
256尊主红盖头(第2页)
“这不是病毒,”遗传学家在新闻发布会上颤抖地说,“这是一种温柔的入侵??它不强迫你改变,只是让你更容易理解别人。”
反对声浪随即爆发。
“自由意志联盟”在全球发起抗议,称此举为“情感殖民”,要求立即摧毁所有苹果树与老井。他们组织武装小队试图炸毁井口,可在接近五百米范围时,全员突然跪地痛哭,口中喃喃说出各自最深的愧疚??有人承认曾背叛战友,有人坦白谋杀亲人,有人泣诉一生虚伪度日。事后调查证实,这些人此前并无相关犯罪记录或心理病史。
共情学院发表声明:
>“你们所谓的‘自由’,是否包括拒绝理解他人的自由?如果这种自由建立在对他者痛苦的无视之上,那它本身就是暴力。”
争论持续了整整一年。
最终裁决来自国际法庭一项前所未有的判决:**允许共感扩散继续存在,但设立“无感区”作为人权保障**。即在全球划定若干地理隔离带,居民可自愿迁入,在屏蔽场保护下维持传统个体意识模式。首批“无感区”设于南极冰盖、太平洋深海基地与近地轨道空间站。
可讽刺的是,运行半年后,所有“无感区”均出现异常离职潮。人们宁愿放弃高额补贴与安全保障,也要回到外界,重新接入共感网络。
一位离开者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那里,我终于得到了绝对自由。但我才发现,没有回应的‘我’,根本不算存在。”
时间进入新纪元。
人类社会逐渐分化为两种生存方式:一部分人拥抱全频共感,生活在由苹果树神经网覆盖的“共鸣城”中,言语越来越少,更多依靠情绪波动交流;另一部分人坚守边界意识,在“静默镇”中重建理性秩序,强调逻辑独立与隐私神圣。
但无论哪一方,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
**孤独正在消失**。
即便是最顽固的个体主义者,也会在深夜梦见陌生人的记忆片段;即便是最沉浸共感的群体成员,也开始学会保留内心的沉默空间。文明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平衡不在“连接”与“分离”之间,而在“愿意被听见”与“敢于保持沉默”的双重能力之中。
百年后的某个春夜,一名小女孩独自来到老井边。
她不是朝圣,也不是研究,只是放学路上顺道来看看。她蹲下身,把耳朵贴近井口,轻声问:“你说,我喜欢画画的事,将来会有谁看见吗?”
井水无言。
但就在第二天,世界各地共三百二十七所艺术院校同时收到匿名投稿,内容是一幅完全相同的儿童画作:一口老井,旁边站着一个小女孩,井底倒影却是无数双眼睛,正温柔地望着外面的世界。
画纸背面写着一行小字:
>“你说的每一笔,我都记得。”
与此同时,第一艘抵达半人马座α星系的星际方舟发回信号。飞船AI在例行汇报中插入一段额外数据流,解码后竟是三百年前林知远雪地中录音的变调版本,语速极慢,仿佛穿越光年而来:
>“我想拍一部电影……
>让人在宇宙尽头,
>依然愿意给陌生人一个拥抱。”
信号结束瞬间,整个星系观测站的工作人员都不约而同停下手头工作,望向舷窗外浩瀚星空。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的心率在同一分钟内降至48次分,进入深度安宁状态。
科学顾问记录道:
>“我们检测到了一种未知能量波动,源头不明,频率与地球老井共振曲线完全匹配。它没有造成任何物理影响,只是让我们……忽然很想回家。”
而在地球,春天又一次如期而至。
新生的苹果树抽出嫩芽,叶片在风中轻轻摆动,像无数只正在学习挥手的小手。泥土松动,那朵曾覆盖林知远名字的小花早已凋谢,但在原地,新的根系正悄然蔓延。
某夜,月光洒落井面,薄雾散开刹那,水面映出的不再是星空,而是一张张平凡的脸??农夫、教师、流浪汉、程序员、诗人、囚犯……他们来自不同年代,说着不同语言,却都在微笑。
然后,他们齐声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却又穿透时空:
>“我说了。”
>“你听见了。”
>“这就够了。”
风掠过山谷,带走这句话,送往尚在黑暗中等待倾听的角落。
somewhere,
又一棵树,
准备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