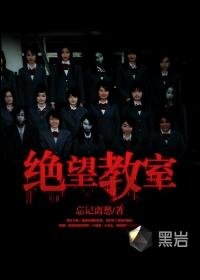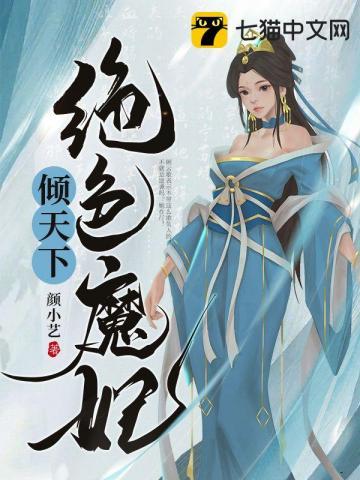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丫鬟打工日常 > 第 93 章(第1页)
第 93 章(第1页)
谢渊迎着夕阳最后一抹余晖踏进谢家主宅,大门前早有下人候着,立时将他往绿水轩方向引。
他原以为来人是崔卯,一路都在想着要如何套话。
然而当看到谢集英身旁那陌生的人影时,谢渊怔了一瞬,面上浮现出几分迷茫。
绿水轩临水而筑,眼下暮色渐沉,四面长窗大开,水面倒影仅余朦胧轮廓,随风拂过时碎成一片黯淡涟漪。
那身穿锦衣的年轻男子背手而立,眉眼间与崔卯有几分相似,却比崔卯更锋芒毕露。
谢集英看到谢渊回来,笑意温和地为二人引荐。
“贤侄,这便是我家阿渊,他在城外书院上学,每日都要这个时辰才能回来,让你久等了。”
随即又转向谢渊介绍道:“这位是崔县令家的五公子。”
果然是崔卯之子。
谢渊心下了然,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一道带着审视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他眼睫半垂,抬手见礼:“见过崔公子。”
崔明远的目光在他身上转了一圈,眼前的少年不过十几岁,长相出众,却异常地沉稳内敛,乍一看出色得让人无可挑剔。
更不用说他如今已是廪生,若是出身世家,前途真是不可限量。
然而却偏偏是商户。
崔明远眼中浮现出几分挑剔,却还是客气道:“前段时日家中设宴我不在,错过了与贤弟相识的机会,事后听家父对贤弟赞赏有加,我实在好奇。今日一见,果然是少年英才,不同凡响。”
谢渊正猜测他的来意,听到这意味不明的几句话,心中反而更加迷惑。
崔卯无缘无故提起自己做什么?
谢渊可不会觉得是因为自己有多惊才绝艳,才让崔卯高看一眼。
他心中越发警惕,面上却不动声色:“崔公子过誉了,不过是先生教导得法,又蒙崔大人宽和垂爱,实在当不得英才二字。”
而崔明远见他态度谦和,也没有因自己的身份便刻意逢迎,脸色倒是缓和多了。
两人沿着长廊踱步闲聊,崔明远又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平日里都爱做些什么,在城外书院上学,来回可辛苦之类的琐事。
谢渊想打听他的来意,对崔明远的提问皆耐心作答,就连他说起些杂学喜好,谢渊也能搭上一两句。
二人相谈不过寥寥数语,暮色便又深重了几分。
然而就在这短暂的交谈中,崔明远却已对谢渊另眼相看起来。
“我平日喜好不多,养这素心兰算一个。只是我费尽心思,又雇了花匠日日照料,却总是不尽人意。贤弟是从何得知,养这素心兰需在辰时之后遮阴的法子的?可是平时也有此等喜好?”
崔明远出身世家,平日里除去难以避免的俗务外,喜爱一切风雅之事。
本以为这人商户出身,虽然考了功名,却未必有什么见识。
没想到相谈下来,他博文强识,娓娓道来,相处起来比起自己那群友人也不差什么。
要知道他可比自己还要小七八岁,却已如此沉稳,真是难得。
谢渊缓声回道:“我并不如崔公子般有这等雅兴,只是平日闲余爱看些杂书,才偶然间得知。若崔公子不介意,回去可让花匠按这法子试试,兴许会有意外之获。”
谢渊说得面不改色,其实爱看杂书的人却是杨桃。
只要不是诗经典籍,她都看得津津有味,话本游记最好,农书星象也不挑。
且她看书从不肯老老实实看,不仅爱在他耳边嘀嘀咕咕,还总喜欢去寻求答案。
如她在书上看到“插者弥疾”时,隔日就要跑去果农那里求证,是不是这样种梨结果就会更快。
虽然关于“素心兰”的种植,花商不肯将种植的法子透露给她,且因她嫌那兰花太贵,自己既舍不得买,也不肯让他当这个“冤大头”,所以这法子便没法验证了,但谢渊还是在她的念叨里记住了那娇贵兰花的养护法子。
崔明远这会儿却因此对谢渊生出几分“如遇知音”的感觉来,就连面上笑意都多了几分真诚。
一旁的谢集英看二人相处甚欢,心中宽慰的同时也隐隐生出一股带着野心的自豪。
谢家的生意越做越大,需要打点的地方也越来越多,而他没有入仕空有举人功名,能做的实在有限。
过去他们认为和萧氏是姻亲,且没有其它途径,理所当然地将大部分希望都寄托在萧氏那里,可谁知却将萧氏的胃口越喂越大。
如今家里多了谢渊这个新的希望,谢家为何不能开始尝试着走向另一条门路?
柏岭崔氏虽不如萧氏的名气大,可他们一族却大都扎根在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