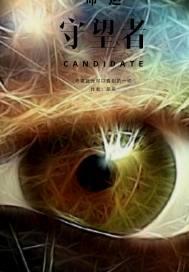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替嫁后夜夜痴缠,殿下他不对劲! > 第255章(第2页)
第255章(第2页)
李玄尧却是面无表情,唯有满眼的醉意弥漫在眼底,未掺杂半点情绪进去,就好像一个是夜色下的深渊,一个是白日里的冰河。
看着看着,收回酒壶,他叹了口气。
像是像,可眼神骗不了人。
江箐珂就从来不会用这种眼神看他。
一次都没有过。
在江箐珂的眼里,他不是高不可攀的太子,也不是与众不同又可怖的怪物,而是可以平起平坐的。。。。。。
李玄尧跟疯了似的,自顾自摇头苦笑了起来。
因为他想到了那个词。
姘头?
抬手从玖儿头上摘下一支金簪,李玄尧用簪尖割断了束腰的锦带。
玖儿红着脸,低下了头。
据她所学,男子行此举,通常是要做那事的。
她便乖乖地跪在那里不动,任由李玄尧将她身上的那件凤袍扯了下去,仅留着里面一身雪白的中衣。
曹公公和花容同时低下头去,都在估量着退出寝殿的时机。
唯有喜晴在那里眼睛冒火似地瞪着李玄尧。
太子殿下若是睡别的女子,她管不着。
可别的女子顶着她家主子的脸,让太子睡,喜晴多多少少觉得有些恶心。
待李玄尧摘掉玖儿的凤冠撇到一旁时,曹公公朝花容和喜晴递了个眼色,示意退出寝殿。
可这时,李玄尧却瞧向茶桌上备用的笔墨纸砚,从笔架上取下一支狼毫笔来。
曹公公是个眼里有活儿的,见状,立即上前研磨,然后躬身退到一旁。
笔尖润满墨汁,他提笔在玖儿两侧的面颊上,分别写了两个字。
宁缺,毋滥。
随手将那支狼毫笔扔到堆叠在地的凤袍上,任由墨渍在缂丝上晕染开一片黑色的圈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