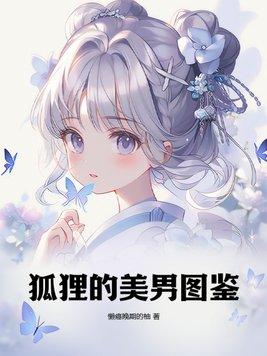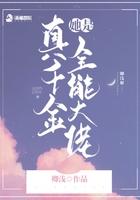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打破教育的“迷思” > 离真正的教育近些再近些(第5页)
离真正的教育近些再近些(第5页)
有一次,姜怀顺看电视节目,心被狠狠地揪痛了。节目报道说,在广西的一个村子里,出了100多个抢劫犯,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而这些抢劫犯的年龄都在18岁到25岁。
记者到村里的小学采访,校长和老师一致说:“我们的孩子很老实,很听话,认真学习,平常没有什么问题。”和学生交流,记者问这些孩子,将来大了干什么?孩子百分之百地回答说:“出外打工挣钱。”
看到这里,一股子热血,直冲姜怀顺的脑门。他大声追问:“教育到底给了孩子们什么?当一个人没有远大的目标和高尚的志趣时,他就不是一个精神意义上的人。他的人生只是在物质层面徘徊,如果不能满足,他怎能不去抢劫、不去掠夺?”
“现在,学生成人化倾向很严重。很小的孩子就知道挣钱、消费,这不是社会深刻的表现,而是一种平庸和媚俗。他们长大后,有知识无智慧,有欲望无理想,有规则无道德,社会该是什么样子!”
他反复跟老师们讲,教育的本质是超越性的,而不是工具性的。
没有情感的注入,没有人性的放大,没有人性中最光辉的诚实、善良、感恩、同情这些有活力的东西,教育就成了驯化。
有一回,听语文老师孙庆晓的课,让姜怀顺感动不已。
课的内容是《诗经·蒹葭》。孙庆晓告诉学生,歌曲《在水一方》就是根据这首古诗改编而成的。学生们兴奋起来,请求她:“老师,你唱唱吧!”
果真,孙庆晓放下教学进程,放声高歌,学生们听得如醉如痴。一曲既了,掌声雷动。
尽管部分教学环节没有完成,但姜怀顺却给了这节课很高的评价。他说:“唱歌仅仅是作料吗?仅仅是增加了一个花絮吗?不是的。唱这首歌恰好就是《蒹葭》的最好的教学方式!”
“只有音乐,才能把学生带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种朦胧的、不可言说的意境之中。依靠单纯的讲解和翻译,怎么能带学生进入这样一种审美的境界?”
在孙庆晓的课堂上,总是充满着音乐。
她认为,音乐的美和文字的美是相通的。美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激**起所有的正面情感,让人对生命有尊崇,对道德有感悟,对信仰有尊崇,对自然有敬畏,对人生的意义,也能有一种全新的把握。
这样的课堂,对学生有着持续的吸引力。如今,孙庆晓所带的班级,不仅成绩优秀,而且连续三年没有一个学生辍学。这在许多农村初中,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上孙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很多学生,都对她的课有着深深的依恋。
“按照美的规律去塑造人,让学生获得一种审美的快乐。”这是同事对她的评价。
只有美的情感,才能让教育触及生命的内核。
而崇高感,则是美的一种极致。
为什么有时会抽出大段时间,甚至是整节课,给学生们讲励志故事、热点时事和自己的哲学思辨?数学老师刘建宇说,是因为“学生是否有崇高的人生目标和志趣,比知识重要得多”。
有一次,刘建宇在网上发现了一篇文章,他特意在班上为学生们朗读。文章的大意是,一个日本记者到中国某大学演讲,演讲前问在座的听众:“谁知道黄继光、邱少云?”没想到,一名大学生抢答说:“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知道这两个傻帽。”日本人由此感慨万分。
文章读完。一位女学生站起来,眼流满面,她问刘建宇:“老师,如果青年人都这样的话,我们中华民族还有希望吗?”
“你就是希望啊,当你落下热泪的时候,就预示着你可能成为明天的脊梁!”
这个学生,刚入学时,成绩在全班居于下游。但从那后,她却迸发出了强大的学习动力。到了初三,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临沂一中。
离校的时候,她对刘建宇说:“我一直记得初一时你读的那篇文章,也因此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学习。”
“要让学生进入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要让他们拥有春水般的情感。”校长姜怀顺由此感悟。
每次交流,他都鼓励老师不要做只关注技巧、在细节上精益求精的“小老师”,而要做“大老师”,做一个站在制高点上、引领学生走向一个更加广阔、丰厚天地的老师。
他说,“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和习惯,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
教育,从来都不只是知识和技能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精神和心灵的格局。
回到北京,翻看资料时,我们看到了校长姜怀顺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几句话:
“教师首先是学生人生成长的导师,然后才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只有当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生活、成长的‘课本’时,教育的真正意义才有可能实现。”
“我们今天所施加的教育,应当被学生视为一件无比高贵的礼物而欣然接受,并成为他们一生的依恋和一世的拥有。”
“教育,必须遵循生命本身的逻辑和教育教学深刻的内在合理性。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希望离真正的教育近些、再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