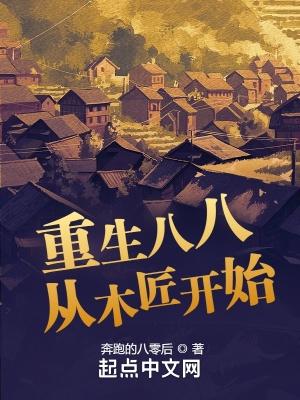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乱臣 > 楔子富贵乡(第5页)
楔子富贵乡(第5页)
正值炎夏,雨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是什么珍稀的东西,等这瓢泼停了,阿月才开口:“我想活着。”
这要求似乎很是无理,命由天定,此番情境,更不由人。
但阿月更明白,保命的机会不多。
京使没露出太讶异的表情,连唇角的三分笑都不曾改,他答应了。
这次交谈的时刻甚短,很快老蚂蚱回来。
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疫病,原本精明的男人憔悴了不少,他一过来,先是向京使行了个礼,转而便瞪了阿月一眼,叫她出去。
阿月离开两人交谈的屋子不过半柱香的时间,老蚂蚱便出来了。
阿月往门口看了一眼一眼,只见他脸上的笑容收都收不住,似乎得到了什么天大的便宜。
很快,阿月就知道了“大便宜”是什么。
难民营里,老蚂蚱按三六九等将人分成组,组成“徭队”。
“按京使的意思,咱们只要帮忙做些事,就能继续安居在此了。”
人群一片静默,只见京使笑着点了点头,将手中拿的一卷奏疏交给老蚂蚱。
老蚂蚱接过东西,行了个从未如此恭敬的礼,京使朝他一笑,就这么走了。
之后,老蚂蚱抱着那奏疏消失了三个日夜才再出现,刚回来便带着几个新提拔的助力,把人群分得更细。
男壮丁、女织工、童子工……十几人一组,一共分了百十组。
似掐着时辰,才分好宫中便来了人。
穿着甲胄,不是来使。
阿月躲在人群后看领头人和难民队,不说别的,光气魄上就差一截。
官兵来一趟,难民便去了七队。
朝中信佛陀,听人说,是去修庙了。
日子踏上正轨,百十来的队伍分成几波,分别去了中都各地修筑庙宇楼阁,其间去到往生宫的最多。
但她没能跟着上路。
许是觉得她真的没用,分队的前一天,老蚂蚱将她撵了出去。
大概不能说撵……阿月回忆那一天,老蚂蚱将她单独叫去,说了许多。
总结下来只一句——这里不留吃白饭的,你没什么用了,拿点吃的用的走吧。
阿月答应了,从此,就开始自己流浪,不再跟着谁。
她就这样躲在每个角落,一面躲,一面尽力的往身上裹泥,裹到别人看不出她是男是女,是人是畜。
去往生宫的队伍越来越多,回来的却很少,有次她偷偷回去,发现营寨了几近空了。
没人认出她。
又两年,熟悉的人几乎都死光了,没人再叫她阿月,渐渐的,那群人给她取了个诨号“泥猴子”。
它站起身,跟着脚印走,一直到往生宫门外不远处停下。
朱门大开,石墙半垒。
它看到一张慈悲的佛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