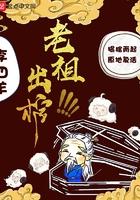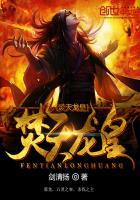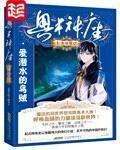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 > 一诗性的自我创造与个人生活的目的(第1页)
一诗性的自我创造与个人生活的目的(第1页)
一、“诗性”的自我创造与个人生活的目的
我们认为,个人主体性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体现在“个人生活的目的”这一问题上。个人在回答和解决“个人生活的目的”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其主体性将得到充分的彰显。在本节,我们将深入哲学史,围绕这一课题,探讨个人主体性被遮蔽的思想根源,并寻求如何彻底克服这种遮蔽,捍卫个人主体性不可代替和还原的存在空间。
(一)形而上学的“脚本”与个人生活的“普遍化”
作为区别于社会共同体的个人,如何理解其生活的目的?按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个人生活的真正目的,就是突破时间、现象和个人意见,与某种超验的事物建立起联系,进入另一个代表永恒真理的世界。这种超验的事物和永恒的世界代表着“人性”的完全实现和人的“本质”的完成,因而也就意味着个人一劳永逸地从无常、奴役、苦难中摆脱出来,实现彻底的“解放”。
根据这种观念,个人的“真理”在于抽象掉生命个体的私人性和个性而形成的“人的共相”,因此,“个体生命”与“人的整体”、“人的公共性”即“社会整体”遵循着同一个游戏规则,二者有着完全相同的目标、相同的理想、相同的活动法则,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完全等同和重叠关系:既然个体生命的根据和价值源泉不在于“个体生命”本身,而在于由抽象掉“个体生命”的私人性和差别性而形成的“人的共相”,那么,对于所有的个体生命来说,它所遵循的游戏规则不能是个体性、私人性的,而只能是同一性和普遍性的,这一游戏规则以“人的共相”为依据,为每一个生命个体“公共”地分有,对所有的千差万别的生命个体都具有普适的约束力,它相信,“所有时代所有人的终极目标,其实是一样的”,“一组普遍而不变的原则支配着世界”,“并且这些规律是真实的是可以获知的”[1]。为了遵循和服从这一公共、普遍的游戏规则,生命个体必须自觉地放弃其私人的“偶然性”,而服从这一公共、普遍的法则。
仔细分析,我们这种对个人生活目的的理解包含三个最为根本的环节:其一,“逃离偶然,拥抱普遍”;其二,“否弃时间机缘,追求必然和永恒”;其三,“远离人的‘实存’,实现人的‘本质’”。
“逃离偶然,拥抱普遍”,即是说,它把“偶然性”视为威胁个人生命价值因而必须被抛弃的敌人,只有超越偶然并努力成就普遍性,个体生命才能找到归宿和着落。偶然性意味着无常和混乱,意味着个人生命价值的破灭,个体生命价值要么存在于个体生活之外普遍的纯粹理性之中,要么存在于无论个体承受苦难还是死亡都将永恒常存的普遍精神之中,对于这种“普遍性”,人们要么臣服于它,要么就听任黑暗的魔鬼,用疯狂、用知识和道德上的晦暗混沌(偶然性)把自己裹缠起来。
“否弃时间机缘,追求必然和永恒”,即是说,它把“时间”和“机缘”视为个人生命价值的否定者,只有超越时间和机缘并进入必然和永恒的世界,个体生命才能功德圆满。时间和机缘意味着短暂和易逝,意味着个人生命价值的速朽,因此,逃避时间和机缘,达到永恒和必然,乃是个人实现其生命“价值”、完成其人生“使命”的必要条件。
“远离人的‘实存’,实现人的‘本质’”,即是说,这种“游戏规则”认为人的“本质”优先于人的“实存”,坚持个人生命的真实价值在于否弃“实存”而抵达其本质。所谓“实存”,指的是人的“个体此在”,指个人在时间和机缘中的偶然性存在,根据这种游戏规则,个人的“实存”归属于个人的“本质”,而个人的“本质”是普遍性、必然性的先验原则,它代表的是一个超越“个体实存”的“大写的人”,皈依“本质”,即是要抛弃感性、偶然的作为“实存”的“小我”,而与“大写的人”合一。
深入探究,可以发现,当“逃离偶然,拥抱普遍”、“否弃时间机缘,追求必然和永恒”、“遗忘人的‘实存’,追逐人的‘本质’”成为个人生命价值设定的的主要内容时,其中所运用的正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在对待个体生命时,它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现实的“个体生命”本身,而是“个体生命”之外和“个体生命”之上普遍的、永恒的作为“本质”而存在的“人性”,即把所有的个性和差别性都清除掉之后所剩余的、为所有生命个体所共有的“人的共相”。这种理解方式最根本的后果便是:个体生命的生存活动失去了属于“自我”的独立的游戏规则而被迫服从“同一性”、“普遍化”的游戏规则,一句话,生命个体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其本己的“自律性”和“私人性”,它使人的个体生命呈现出如下景象。
(1)人的生命的“个体性”是先验的普遍实在的“外化”物,人的“一般”优先于人的“个别”,人的“个别”是人的“一般”的构成物。众所周知,在柏拉图那里,“个体性”只有通过“分有”普遍性的“共相”,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根据,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在讨论“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时,一方面批判哲学史上其他形而上学家的普遍性是抽象的普遍性,不能容纳个性和特殊性,而自己的普遍性概念区别于抽象的普遍性概念,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它可以将个体性与特殊性统摄并涵盖于自身之内;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与个别性和特殊性相比,普遍性才是“真理”本身,“普遍性”具有真正的“实体性”,“个体性”和“特殊性”是“普遍性”自我区别的、能动活动的产物,是“普遍性”的表现和外化,因此,在囊括了特殊性和个体性于自身之内的普遍性以外,独立自在的个性是根本不存在的。在“普遍性”削平一切的威力面前,人的生命的“个体性”终成虚幻。
(2)个体生命将在先验的、普遍的人的“共相”的先验框架的削平下,过滤、蒸发成彻底清除了差异性、多面性的单极性、单向性存在。按照上述理解方式和思维逻辑,为了获致人的“本性”或人的先验“本质”,必须在人的本来具有“立体性”的多维性质中,区分出现象与本质、理性与感性、永恒和暂时、普遍与个别、表层与深层等二极对立的性质。在二极之中,把前者规定为“人性”和“人的本质”,而把后者规定为人的“现象”和人的“偶性”,于是,以前者为标准来压制后者,在两极之中牺牲其中一极,在二元之中虚化其中一元,就成为建构“人的形象”的必然选择。这样,个体生命中无限复杂、丰富的内容就必然被蒸馏、过滤和挥发掉,以适应这一先验框架的内在要求,很显然,由此形成的个体生命必然是“水晶宫里人不见”,“立体化”的多维性质被“平面化”为单向、单极的存在。
(3)个体的生命活动将遵循着形而上学“脚本”规定好的内容而展开,或者说,个体的存在及其生命历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形而上学“脚本”所蕴含的内容。普遍的、先验的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犹如写就的剧本,安排了“剧中人”的一切活动及其命运,除了扮演好已规定妥当的角色,个人排除了任何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可能。这即是说,按照上述理解原则和思维逻辑,生命个体成为了一种定性化的、被一劳永逸地规定好的、失去了自我生成和自我创造的存在:既然个人生命的生存根据存在于前定的先验“本质”中,而“本质”总是具有永恒、超感性、超时空和超历史的性质,对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人都拥有普遍有效性,那么个体生命必然成为一种已定性的、被先验地完成了的存在,成为一种禀赋“永恒”的超历史本性的存在。
(4)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将成为由外在规范来予以评判和定义的对象,个体生命的价值将因此而失去其“自成目的性”。按照这种理解方式和思维逻辑,个体生命的价值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遍、先验的“人性”或“人的本质”,这种“人性”或“人的本质”是个体生命所应予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和标准,它既解释着生命个体的价值和道德价值,也规定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道德生活,因而构成了个体生命意义与无意义、善与恶、好与坏等的强制性规范。这就意味着,个体生命的价值源泉来自于自身之外的超验源泉,在这一超验源泉的规范之下,个体生命本己的、通过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自律性”价值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个体生命失去了自成目的性,而成为了普遍本质、先天人性实现自身的手段。
(二)不能被普遍共相穿透的空间:“个体我在”的正当性
“实存性”这一概念来源于拉丁文“existential”,与“共相”、“一般”、“普遍”相对照,其最基本的含义是“个别性”、“实际性”与“此在性”。它意味着存在者的“如此存在”(tohotiestin),指示着特殊个体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实情。它要回答的是:“那个”(that)存在者“如何”、“怎样”,其关注的中心是“那个”及作为“那个”的“个体存在者”。
人作为生命个体,即是这种“实存性”的存在,或者说,人的生命个体就是“实存”。只有从“实存性”的角度来把握生命个体,生命个体才能如其所是的那样呈现自身,而不至于被普遍化为所有生命个体“公分母”的“人的共相”和“本性”。
使个体生命从“范畴”和“共相”的阴影下挣脱出来,确立其不可还原的个体性与私人性并由此真正通达“个人的真实性”,这是整个现当代哲学的重大主题之一。在一长串的名单中,海德格尔的思考具有枢纽性的重要地位。他上承克尔凯郭尔、尼采,下启福柯、德里达、罗蒂等,并通过其原创性的工作,使得个体生命从形而上学“共相”和“本质”的“轧平”机制中解放出来并获得其真实的存在,成为了一项具有独立意义的思想事业。
在海德格尔之前,克尔凯郭尔也许是最早明确和自觉追问“个体是谁”,即个体生命的“个体性”和“私人性”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终生与黑格尔作战,在他看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家们试图以思辨理性和概念辩证法追寻和建构“存在”,实质是以“普遍”来解释“个体”,以“共相”来说明“个性”,“个人的真实存在”由此而被扼杀和吞噬,克尔凯郭尔所坚持的“个人的真实存在”,就是不能被任何普遍的理性法则和共相原理所还原,具有其别具一格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的“个体实存性”,它比任何普遍理性和抽象共相都更为根本。抵制理性法则对生命个体的抹杀,捍卫生命个体的独立性,是克尔克郭尔毕生的使命。
海德格尔充分肯定克尔凯郭尔的贡献,“在19世纪,克尔凯郭尔就把生存问题作为一个实际生存活动的问题明确加以掌握并予以透彻地思考”[2],“克尔凯郭尔极为深刻地看到了生存上的‘当下即是’现象”[3],但是,他同时指出,“他对生存论问题的提法却十分生疏,乃至从存在论角度看来,他还完全处在黑格尔的以及黑格尔眼中的古代哲学的影响之下”,[4]“他停留在流俗的时间概念上并借助于现在和恒常性来规定当下即是”[5]。在海德格尔看来,正因为这些缺陷,克尔凯郭尔对个体生命的追问仍然是半途而废的。
克尔凯郭尔之后,尼采是把“个体生命的真实性”作为主题的另一重要哲学家。他清楚地看到,柏拉图主义把人的最高价值置于彼岸的超感性的理性世界,个体生命的价值完全为后者所规定,这实质上是对个人生命真正价值的否定。对于尼采的这一洞见,海德格尔概括道:“此在基本力量的主要虚弱化就在于对‘生命’本身的建立目标的力量的诽谤和贬低。而这种对创造性生命的诽谤的原因又在于:在生命之上被设定了那种要求否定生命的东西,这种要求,这种理想,就是超感性之物,它被解释为真正的存在者。”[6]由此必然带来“虚无主义”的结局:“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对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7]正因为此,尼采把“重估一切价值”和“为人生作辩护”作为自己的使命。“重估价值”,最根本的就是要重估“个体生命的价值”;“为人生作辩护”,就是要捍卫和提升个体生命健康而非颓败的生命力量。
海德格尔同意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虚无主义本性的诊断,但是他认为,尼采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差异仅仅在于他用强力意志代替了主体、实体、共相等来充当形而上学的实体,因此尼采仍然属于形而上学。也正因为此,尼采不可能通达真正个体生命的“此在”,当他强调宇宙是强力意志的永恒轮回,个体生命作为强力意志的表现形式,与宇宙的“大生命”相比,不过是“小生命”,因而应该融入宇宙生命的全体之时,尼采就充分暴露了其形而上学的本性,个体生命被宇宙的“大生命”所溶化,个体生命的“个体性”与“私人性”最终没能逃脱形而上学实体的阴影。
海德格尔指出,人的实存或人的此在区别于人的“范畴存在”,在于它具有如下特性:(1)此在不是一种“现成”的存在,其根本特性在于其“生存”,“此在无论如何总要以某种方式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我们称之为生存”[8],“此在的‘本质’根基于它的生存”[9],“人的‘实体’不是综合灵魂与肉身的精神,而是生存”[10]。正是这一点,使得此在区别于其他存在者而具有特殊的存在方式。(2)所谓“生存”,是指此在所具有的“可能性”,“此在一向是它所能是者;此在如何是其可能性,它就如何存在”[11],“此在是委托给它自身的可能之在,是彻头彻尾被抛的可能性。此在是自由地为最本己的能在而自由存在的可能性。在种种不同的可能的方式和程度上,可能之在对此在本身是透彻明晰的”[12]。(3)此在的根本特性是“时间性”,“时间性”构成了此在“存在的意义”,“在隐而不彰地领会着解释着存在这样的东西之际,此在由之出发的视野就是时间”[13]。就此而言,此在作为生存可能性,“有别于空洞上的逻辑可能性。它也有别于现成事物的偶或可能,……作为生存论环节的可能性却是此在的最源始最积极的存在论规定性”[14],“时间性”乃是对此在存在意义的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遮蔽人的“此在”,从而导致“此在”存在意义被遗忘的根源。传统形而上学自柏拉图以来,长期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人于是被归结为“理性”的“共相”,海德格尔明确地把这种观点称为“动物学的观点”,在《存在与时间》等著作中,他通过对笛卡尔、康德等人的批判,解构了这种“动物学观点”对生命个体的“我性”或者说“私人性”的掩蔽。人们常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视为近代哲学的开端,“我思”的凸显本在突出“我”的基础地位,但海德格尔指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恰恰是以生命个体的“我性”或“私人性”的耽搁为前提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笛卡尔把“自我”规定为“我思”时,实际仍是把“自我”当作一个“普遍之物”来看待的,“自我”被当成“实体”,一个禀赋先验理性的“思维实体”,因此,笛卡尔的“自我”仍是一个“共相”、一个“普遍存在”,而非作为“专名”而存在的“实存”。对此,海德格尔说道,“笛卡尔把中世纪的存在论加到他设立为fuumin(不可动摇的基础)的那个存在者身上,以此来进行他在‘沉思’中的基本考查。Ress(思执)从存在论上被规定为ens(物)”[15],因此,“他在这个‘基本的’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正是这个思执的存在方式,说得更准确些,就是‘我在’的存在的意义”[16]。这也就是说,笛卡尔没有真正理解作为能思之物的“我”的存在方式及其存在的真实意义,因而最终窒息了“我”的“实存”性质。相对于笛卡尔,康德对“我”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有所推进,“在康德的分析中有两重积极的东西:一方面他看到从存在者层次上把‘我’引回到一种实体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坚持‘我’即是‘我思’”,“‘我思’等于说:我维系”[17],因而“我思”不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自因实体,然而,康德“又把这个‘我’把捉为主体,因而是在一种从存在论上来说不当的意义上把捉这个‘我’的。因为主体这一存在论概念所描述的不是‘我’之内自身的自身性,而是一种总已现成的事物的自一性与持存性。从存在论上把‘我’规定为主体,这等于说:把我设为总已现成的事物。‘我’的存在被领会为ress(思执)的实在性”[18]。在此意义上,无论是笛卡尔,还是康德,都把“此在”理解为了具有“自一性”与“持存性”的现成事物,“此在”被“普遍化”因而使之失去了“自身的自身性”,即失去“此在”真正的“我性”和“私人性”。
海德格尔把“时间性”作为此在领悟自身存在得以可能的境域,通过对此在“有限性”的揭示,从根本上解构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对个体生命的遮蔽,为生命个体彻底摆脱抽象“人的共相”或“人的本性”的专制,回归不可剥夺的“私人性”和“个别性”,开辟了一条极为重要的道路。
如前所述,此在的本性就是“生存”,而“生存”意味着“可能性”,意味着此在“能够在其最本己的可能性中来到自身,并在这样让自身来到自身之际把可能性作为可能性保持住”[19],而“保持住别具一格的可能性而在这种可能性中让自身来到自身,这就是将来的源始现象”[20]。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将来的源始现象”就是“时间”:“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将来。”[21]在此意义上,“时间性问题”就是此在本源意义的生存可能性问题,生存于世的此在,其存在意义在根本上是“时间性”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时间性”并非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家们所理解的“永恒性”,恰恰相反,形而上学的“时间观”恰恰是以抹杀和遗忘真正的“时间性”为代价的。真正的“时间性”乃是“有限性”,它意味着:此在的生存有一被给予的终结,这就是“死亡”。这是此在超越寻常的生存可能性。因此,此在作为“能在”,其根源在于“死亡”、在于“生存之终”,对此,海德格尔说道,“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已经被抛入了这种可能性。它委托给了它的死亡而死亡因此属于在世”,[22]“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23]。因此,此在本源性的时间性乃是一种有终结的、有限的时间性,“此在以出生的方式生存着,而且也已在向死存在的意义上以出生的方式死亡着。……在被抛境况与逃遁或先行着向死存在的统一中,出生与死亡以此在方式‘联系着’。作为操心,此在就是‘之间’”[24]。因此,此在本源性的时间性与“永恒现在”的形而上学的“流俗时间观”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有限性”和“历史性”的。正因为此,此在永远不能如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所设想的那样达到与“终极实在”和“永恒本质”的接触,而总是一种处于时间之中的有限和历史性的生存,对此,海德格尔说道:“正是出于为形而上学奠基的意图而对有限性的最内在本质的强调,本身就必须永远是有限的,永远不可能成为绝对的。”[25]
以本源“时间性”为境遇,凸显出此在的“有限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抵达个体生命独具一格的、不能被形而上学的共相所吞噬的“私人性”和“个体性”。
在“杂然相处的常人状态”中,一个此在可以由另一个此在“代理”,此在被“他人”所宰治因而丧失了自己本己的“个别性”和“私人性”,之所以如此,根源就在于“作为沉沦着的存在乃是在死亡面前的一种持续的逃遁”。然而,一旦人们领会到死亡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而又无可逾越的可能性”,此在就将从“常人状态”状态中超拔出来,发现和确证自己不可替代的“别具一格”的“个人性”和“私人性”。对此,海德格尔说道:“死是把此在作为个别的东西来要求此在。在先行中所领会到的死的无所关联状态把此在个别化到它本身上来。这种个别化是为生存开展出‘此’的一种方式。这种个别化表明,事涉最本己的能在之时,一切寓于所操劳的东西的存在与每一共他人同在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当此在是由它自己来使它自身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此在才能够本真地作为它自己而存在。”[26]“死亡”使此在“个别化”,是因为它是无法被任何人所替代的、纯属个人私人的事情,面对死亡,没有人可以代为承担,此在因此而成为“独一无二”、必须自我负责的存在,“任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27],“在‘终结’中以及在由‘终结’组建的此在整体存在中,本质上没有代理”[28],“死确乎意味着一种独特的存在之可能性:在死亡中,关键完完全全就是向来是自己的此在的存在。死显现出:死亡在存在论上是由向来我属性与生存组建起来的”[29],在这种个人性的本源时间中,个体生命不可由形而上学的“共相”所敉平和取消的“私人性”和“本己性”由此而得以真正的确立。
在海德格尔这里,“时间性”不是此在的“本质属性”,或者说不是此在的“共相”,而是此在通达其本真的个体性和私人性的源始境域,“时间性”意味着此在的“有限性”,意味着此在通过对这种“有限性”的领悟摆脱形而上学的共相的专制而使“个人”真正成为“个人”。海德格尔曾这样说:“本真的时间就是从当前、曾在和将来而来的、统一着其三重澄明着到达在场的切近。它已经如此这般地通达了人本身,以至于只有当人站在三维的达到之内,并且忍受那个规定着此种到达的拒绝着—扣留着的切近,人才能是人。”[30]海德格尔通过对人的有限性的揭示,消解和割断了形而上学的普遍实体和抽象共相对生命个体的支配关系,并昭示了一个人们经常企图闪避不予面对和承认的一个事实:个体生命是不可能真正达到“万寿无疆”的,企图逃避时间,遁入永恒,通过与某种超验的实体和绝对本质合二为一,来达到“无限性”,不过一种自欺和逃避,勇敢地直面人的“有限性”,自律地度过那必有一死的有限生命,恰恰正是个体生命忠实于自身、真诚无伪地生活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