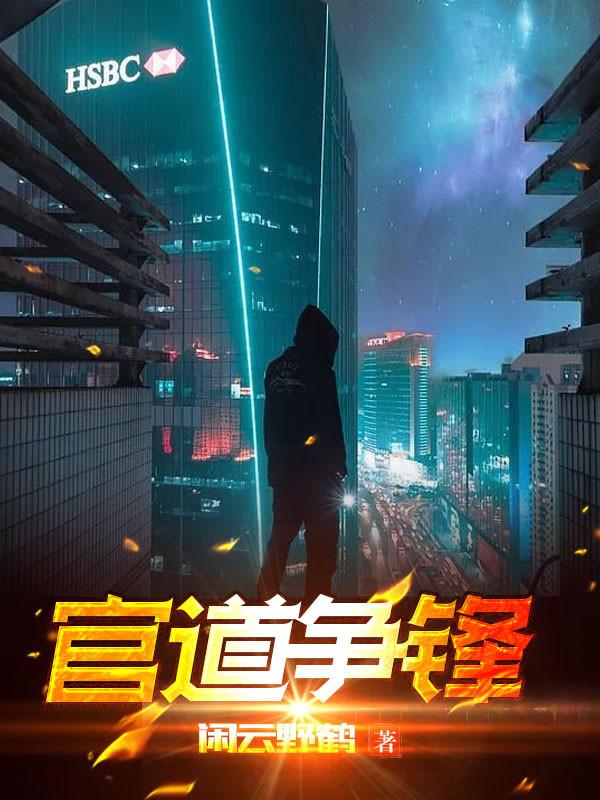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戍光志愿雄赳赳 > 第十四章意外的盟友(第1页)
第十四章意外的盟友(第1页)
嘉梁的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
不是暴雨,是缠缠绵绵的细雨,像一层薄薄的纱,裹着古城的青瓦、后山的草木,也裹着马家四代人沉甸甸的心事。社区会议后的分歧愈演愈烈,支持旅游开发的居民在街头贴出了“拒绝守旧,拥抱发展”的标语,甚至有人在老年人协会的院墙外涂鸦,写着“戌光志愿者滚出嘉梁”。旅游公司更是趁机反扑,通过本地媒体发布“生态步道将带动就业,守护派阻碍民生”的通稿,把马家父子推到了“民意对立面”。
马向东家的堂屋,气氛压抑得像要滴出水来。煤油灯的火焰被风吹得微微晃动,映着四张疲惫的脸。马建国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居民的反对意见,还有旅游公司新抛出的“优惠政策”——承诺给每户支持开发的家庭发放两千元现金补贴。马援朝刚从消防队回来,教导员虽然不再施压,但同事们的议论让他如芒在背,妻子王秀兰依旧在娘家,电话不接、信息不回。马远对着电脑屏幕,眉头紧锁,他发布的澄清视频被旅游公司买了水军恶意举报,平台已限制传播,评论区满是“收了钱抹黑企业”的恶意揣测。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马建国叹了口气,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旅游公司有钱有势,还会煽动民意,我们光靠嘴说,根本没人信。”
马援朝沉默着,手里的茶杯凉透了也没喝一口。他知道,没有实打实的证据,这场斗争迟早会被利益和谣言淹没。
马远猛地合上电脑,一拳砸在桌上:“太欺负人了!我们有测绘数据,有地质监测报告,可他们根本不看,只知道造谣!”
马向东坐在主位,手指依旧摩挲着那张三合一的地图,眼神却没有丝毫动摇。“别急,”他的声音沙哑却沉稳,“守护家园的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当年在长津湖,我们被敌人包围,弹尽粮绝,不也等到了援军吗?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援军?”马远苦笑,“现在谁还会帮我们?社区里的人被分红迷了眼,上级被关系压着,网上全是嘲讽,我们就是孤家寡人!”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雨水敲打门板的声响。“有人吗?请问马向东爷爷在家吗?”一个清脆的女声在雨夜里响起,带着一丝焦急。
马建国站起身,疑惑地走向门口。这个时候,会是谁?
打开院门,雨幕中站着一个年轻女孩。她约莫二十四五岁,穿着冲锋衣,裤脚沾满泥水,背着一个沉重的登山包,头发被雨水打湿,贴在脸颊上,却难掩一双明亮的眼睛,像雨后的星辰。她的胸前挂着一个工作证,上面写着“省城地质大学索娜”。
“你是?”马建国警惕地问道。
“爷爷您好,我叫索娜,是省城地质大学的研究生。”女孩语速飞快,眼神坚定,“我跟着导师的团队,一直在监测嘉梁的地质环境,看到网上的争议,还有你们发布的调研数据,我觉得……我们可能掌握了更关键的证据。”
马向东听到声音,拄着拐杖走了出来。“进来说。”
索娜跟着走进堂屋,卸下登山包,从里面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叠厚厚的报告。“马爷爷,马叔叔,马大哥,”她分别称呼着,手指快速打开电脑,屏幕上跳出一组组复杂的地质监测数据和三维模型,“我们团队从三年前就开始监测嘉梁后山的地质结构,这里是典型的‘层状滑坡体’,山体由松散的砂岩和黏土交替构成,稳定性极差。”
她指向屏幕上的红色区域:“你们看,这是近一个月的监测数据,旅游公司的勘探和违规施工,已经导致山体内部的剪切带活动加剧,滑坡预警等级从‘黄色’提升到了‘橙色’。如果真的修建索道,施工中的爆破、桩基开挖,会直接触发大型滑坡,不仅会掩埋羌人古墓群,还会冲毁山下的居民区,堵塞三江河道!”
马远凑近屏幕,眼睛一亮。索娜的数据比他的测绘更精准,涵盖了山体内部的应力变化、地下水脉的流动异常,甚至模拟了滑坡发生后的影响范围,和他之前的监测结果完全吻合,却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你说的是真的?这些数据经得起推敲吗?”
“绝对经得起!”索娜肯定地点点头,从报告中抽出一份盖着省城地质大学公章的监测结论,“这是我们导师团队联合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出具的正式报告,已经提交给了省自然资源厅。我们本来想直接联系当地政府,可旅游公司的关系网太密,报告根本递不上去。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坚持,就想,或许我们可以联手。”
马建国接过报告,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专业数据和权威公章,激动得手都在颤抖。“好!好!有了这份报告,我们就有了科学依据,看旅游公司还怎么狡辩!”
马援朝也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索娜的出现,就像一场及时雨,给陷入绝境的他们带来了希望。
索娜看着马向东,眼神里满是敬佩:“马爷爷,我听说了您的故事,还有这张地图的来历。您用一辈子守护这片土地,这种坚守,让我们这些学地质的深受感动。我们研究地质,不是为了纸上谈兵,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这片土地的生态和历史。”
马向东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孩子,谢谢你。守护家园,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代人的事。你们年轻人有知识、有技术,比我们更有力量。”
就在这时,院门外又传来一阵脚步声,这次是急促却沉稳的。马建国再次打开门,看到县文化馆的老馆长周明远,手里抱着一个沉甸甸的木盒,浑身湿透,却紧紧护着木盒,生怕被雨水打湿。
“周馆长?”马建国愣住了。周馆长今年六十岁,即将退休,一辈子都在文化馆工作,性格沉稳,不善言辞,之前社区会议时也在场,却一直沉默不语。
周明远走进堂屋,抹了把脸上的雨水,目光落在马向东身上,又看了看索娜和她的报告,缓缓说道:“马老班长,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这些天,我翻遍了文化馆的尘封档案,终于找到了这个。”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盒,里面是一叠泛黄的宣纸和几本线装古籍。“这是民国时期的《嘉梁县志》孤本,还有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的原始记录。上面明确记载,后山‘瓦屋坡’一带,有‘羌人故墟,墓群绵延数里,出土彩陶、青铜剑若干’,被列为‘待保护古文化遗址’。只是后来年代久远,普查记录被遗忘在档案库,加上后山交通不便,一直没有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才让旅游公司钻了空子。”
他拿起一本线装古籍,翻到其中一页,上面用毛笔写着:“瓦屋坡者,羌人圣地也,背依神山,前临三水,墓群之下,藏水脉,护嘉梁,毁则地气绝,水脉枯。”
马向东看着古籍上的文字,激动得眼眶都红了。这与他地图上的标注、与索娜的地质监测数据,完美印证!“没错!就是这样!后山不仅有古墓,还是水脉之源,毁不得!”
周明远叹了口气:“我在文化馆工作了三十年,一直觉得对不起这份档案,对不起这片土地的历史。眼看就要退休了,要是让古墓毁在我手里,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马老班长,你们的坚持,点醒了我。守护历史,守护文化,是我的职责,我不能再沉默了。”
堂屋里,所有人都沉默了。索娜的科学数据,周馆长的历史档案,马向东的老地图,马远的测绘结果,马援朝的地质监测,马建国的实地调研,像一块块拼图,终于拼凑出完整的真相——后山是地质脆弱的“滑坡体”,是承载千年历史的“羌人古墓群”,是滋养古城的“水脉之源”,任何大规模开发,都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太好了!”马远激动地说道,“现在我们既有科学依据,又有历史档案,还有实地调研数据,旅游公司再也无法狡辩了!”
“还不够。”马向东冷静地说道,“旅游公司不会轻易放弃,他们肯定会质疑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我们需要把这些证据整合起来,提交给上级部门,同时向公众公开,让所有人都知道真相。”
索娜点了点头:“我已经联系了省自然资源厅的领导,他们答应明天派工作组下来实地考察。只要他们确认了我们的数据,旅游公司的项目就必须停工。”
周明远也说道:“我会联系省文物局,带着档案和古墓碎片,申请将羌人古墓群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旦列入保护名录,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擅自开发。”
马建国站起身:“我现在就组织戌光志愿者,分成两队,一队去社区宣讲,带着证据让居民们看清真相;另一队去整理所有材料,准备提交给工作组和媒体。”
马援朝也说道:“我去联系消防大队的同事,他们对地质灾害的危害有深刻认识,或许能争取到更多支持。”
马远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充满了感慨。曾经的孤家寡人,如今却汇聚了如此强大的力量——有老一辈的坚守,有中年人的担当,有年轻人的冲劲;有历史的厚重,有科学的严谨,有实践的务实。这场跨越年龄、跨越领域的联盟,因为共同的守护信念,悄然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