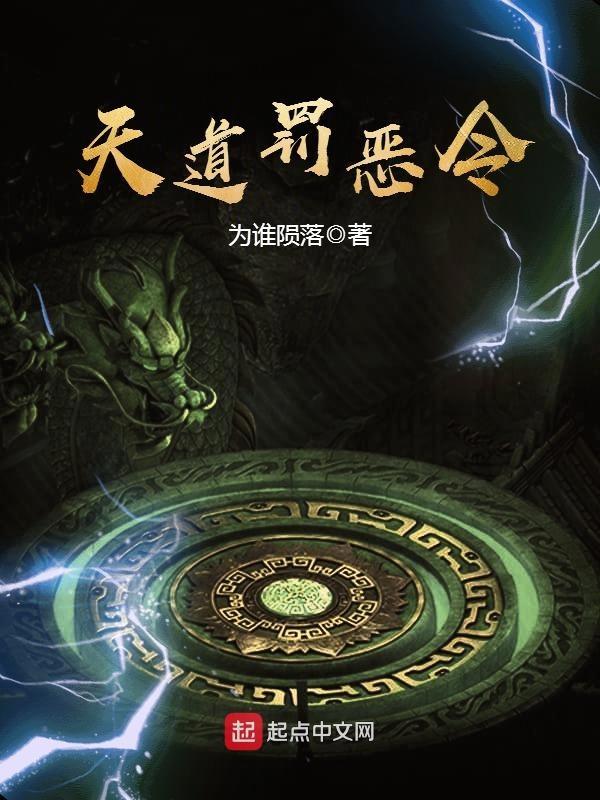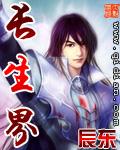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 > 三孔子 未知生焉知死(第2页)
三孔子 未知生焉知死(第2页)
[1]参见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170页。
[2]韦伯同时认为:“中国人在日常交谈中开口不离金钱与金钱利益。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从这种无休止的、强烈的经济劳碌与经常遭到抱怨的极端的‘实利主义’中,并没有发展出伟大的、有条理的、理性的经营观念,而这些观念,至少在经济领域里,曾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只有广东人是个例外,在他们那儿,由于过去外来的影响,加之现在有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进逼,才学会了这些观念。”(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黑体为引者加)
[3]参见韦伯:《儒教与道教》第六章,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196页。
[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8—19页。
[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3页。
[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3页。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4页。
[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4页。黑体为引者加。
[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4页。
[1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4页。
[1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4—205页。
[1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8页。
[13]徐复观原文如此。按大陆现代普通话的表达习惯,此处“普遍地人间”应为“普遍的人间”。
[14]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黑体为引者加。
[15]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徐复观所论及的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六个方面的地位是:发现了普遍地人间;开辟了内在的人格世界;开始有学的方法的自觉;教育价值的积极肯定和教育方法的伟大启发;整理了古代文献并赋予新的意义;人格世界的完成。(参见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80页)
[16]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黑体为引者加。
[17]参见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8]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9]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黑体为引者加。
[20]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21]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黑体为引者加。
[22]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23]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24]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25]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黑体为引者加。
[26]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27]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