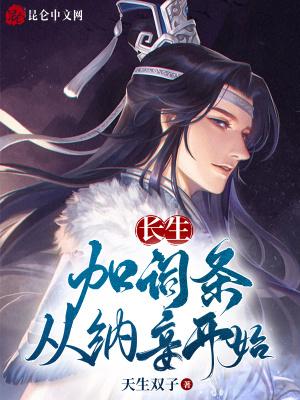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 > 一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及其超越(第2页)
一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及其超越(第2页)
马克思通过“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阐释所体现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人类解放的基本道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55]人类解放的基本条件就在于,理论必须被群众(无产阶级)所掌握才会成为可能和现实。马克思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的历史中,为在现代世界实现理论与实践统一基础上的人的解放,提供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有力论证:“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殊的实践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56]但是宗教改革所体现的理论与实践统一上的成功,还不能为当代的“彻底的德国革命”获得成功提供完全的证明,因为它“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国思想的要求与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回答之间有惊人的不一致,与此相应,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以及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是否会有同样的不一致呢?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57]
已经确立了深厚历史感的青年马克思不是孤立地谈论人的解放,而是从现代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具体的历史的相互关系中来展开论述:“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58]关于德国的解放问题,马克思分析了德国的阶级状况,并在对比了德国与法国的政治解放与普遍解放的不同之后,鲜明地回答了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到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59]。而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和必须担负其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生成和存在标志着现存世界的深刻的矛盾、对立和分裂:“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60]
青年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的理念、性质和追求与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内在地结合、贯通在一起,并由此宣示了在现代世界中这种历史地建立起来的、理论与实践的批判的革命的统一,必将孕育和展露出的人的解放的曙光:“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61]
马克思在结论中再一次从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哲学(理论)与实践(无产阶级的批判与革命)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62]
青年马克思通过历史的权利与人的权利、人的完全丧失与人的完全回复的内在矛盾,充满**地揭示和批判了现代世界实际存在着的深刻对立,并以哲学(理论)与无产阶级(实践)的内在统一为核心原则的彻底的革命,作为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两个世界的内在紧张,在这里表现为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的紧张、矛盾和对立,而超越、扬弃和解决这一紧张、矛盾和对立,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青年马克思通过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的紧张、矛盾和对立,所确立、所阐发的阶级自由和人的解放的主题和格调,在此后马克思整个一生的手稿和著作中、特别是《资本论》中变得越来越具体、系统,越来越清晰、雄厚,成为人类走向以自由的个性与平等为内在灵魂的、最富有思想生机和革命青春的一曲伟大的交响乐章。
[1]处于“对物质利益问题困惑”期的马克思原打算就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下列问题写四篇文章,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问题;关于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纠纷问题;关于林木盗窃法问题以及关于莱茵省限制地产分析的法律草案问题。”第一篇和第三篇刊登在《莱茵报》上,“第二篇即关于科隆纠纷问题的文章因书报检查未能发表,其手稿至今下落不明;而第四篇文章马克思是否写了,写得怎样和手稿处理情况,目前均不得而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的“注释”50,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10—1011页)。
[2]马克思:《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马克思:《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4]马克思:《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34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5]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议会辩论情况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1页。黑体为引者加。
[6]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议会辩论情况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67—168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7]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议会辩论情况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6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8]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议会辩论情况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6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9]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议会辩论情况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9页。黑体为引者加。十多年后的马克思在评论英国之于印度的历史使命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曾把“自由报刊”作为英国重建印度的基本因素之一。
[10]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议会辩论情况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9页。
[11]与黑格尔一再强调基督教原则与现代国家的一致与和解不同,前《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已经看到并一再强调基督教与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不应该根据基督教,而应该根据国家的本性、国家本身的实质,也就是说,不是根据基督教社会的本质,而是根据人类社会的本质来判定各种国家制度的合理性。”(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议会辩论情况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6页)
[12]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17页。黑体为引者加。
[13]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17页。黑体为引者加。
[14]马克思“用理性国家反对宗教国家,……此时马克思研究国家时所采用的是一种价值悬设的逻辑,……他是将社会进步的信念寄托在国家理性的基础上,认为国家理性的完善必将推动历史的进步。”(杨晓东:《马克思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68页)以理性国家作为价值悬设来考察历史的进步与完善问题,表明马克思在这里以理性自由的国家理念审视历史和现实的哲学特征,从而在国家问题上彰显了理念与现实之两个世界的深刻的内在张力。但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此时所展示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后《莱茵报》时期、特别是1845年后的情形存在着重大差异:前者更多地具有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相一致的特征,而后者则由于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出场,更多地凸显了“现有”(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与“能有”(扬弃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张力。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所蕴涵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在1845年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16]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5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7]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5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8]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6页。黑体为引者加。
[19]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6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0]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注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注释93,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18页。
[21]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8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2]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3]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0页。黑体为引者加。青年马克思基于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矛盾,深刻地意识到贫苦阶级的习惯权利并没有反映在体现着有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制度中:“在贫苦阶级的这些习惯中存在着合乎本能的法的意识,这些习惯法的根源是实际的和合法的,而习惯法的形式在这里更是合乎自然的,因为贫苦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有意识的国家制度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应有的地位。”(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3页。黑体为原著者加)而下面这句话更鲜明地道出了形式背后的实质:“盗窃林木者偷了林木所有者的林木,而林木所有者却利用盗窃林木者来盗窃国家本身。”(同上书,第27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5]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9—10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6]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0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3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8]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39—40页。黑体为原著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