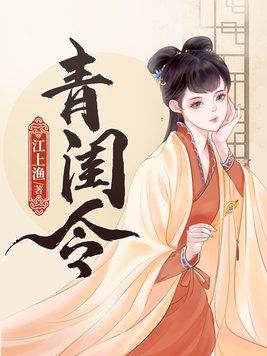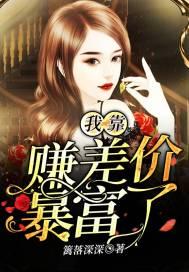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 > 三资本哲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冲突(第2页)
三资本哲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冲突(第2页)
因此具有深厚而巨大的历史感、保持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之内在张力的马克思,是在资本的文明面亦即资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前提和语境下,来展开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这一深刻社会历史变革过程的。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30]
在这里,马克思通过“自由王国”、“社会化的人”、“事物的本性”、“人类本性”、“目的本身”、“彼岸”与“必然王国”、“外在目的”、“盲目的力量”等概念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对立,展示了作为理念的自由王国与现存的必然王国的相互关系,这些意蕴精深的观念、思想和文字深刻地凸显了未来世界的自由王国与现存世界的非自由的必然王国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张力。这两个世界的内在矛盾的历史性的解决,只有在必然王国(资本逻辑)的必然性得到彻底发挥,即以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对立为轴心的现存资本世界,一方面为自由王国的到来创造现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又由于它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必然走向解体和灭亡,只有在这一二律背反的内在矛盾和历史悖论真正彻底的终结之日终于到来之时,人类的自由王国才能真正确立。
这就是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之两个世界的内在矛盾得到彻底解决,从而产生历史观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伦理主义)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的社会历史根源得到彻底消解,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也在彻底解决中走向和解与统一的社会形态。
这就是作为普遍性意义的人的人性和本质完美复归、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确立的共产主义时代。
马克思历史理论即马克思全部哲学—经济学批判中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所具有的青春与生机、魅力与秘密,也由此得到了历史性解答。
[1]详见拙作第七、第八两章:“资本与世界历史”。
[2]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88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89—390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4]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6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5]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95—396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6]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90页。黑体为引者加。
[7]马克思批评斯密、李嘉图不懂得现代世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对立的阶级性质,不懂得资本存在的暂时的和历史的性质,从而他们也就不理解资本与劳动的相互关系的真正秘密。“在斯密那里,资本最初并不表现为把雇佣劳动要素当作自己对立面包含在自身中的东西,……而是表现为来自流通的东西,表现为货币,因而资本是通过节约从流通中产生的。可见,「斯密认为」资本最初不会自行增殖,因为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恰恰不包含对他人劳动的占有。”(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92页。黑体为原著者加)当然马克思接下来谈到:“因为斯密又在地产和资本的形式上把生产资料和生产材料作为独立的形态同劳动对立起来,那他在本质上就是把劳动设定为雇佣劳动。”这说明斯密产生了矛盾和动摇。(同上书,第292页)在李嘉图那里,他“也是把雇佣劳动和资本理解为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形式;这就是说,正因为把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形式本身理解为自然的形式,这些形式本身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因而没有从这种形式同财富形式的一定联系上去理解,而财富本身在其交换价值形式上,则被看作财富物质存在的单纯形式上的中介。因此,李嘉图不理解资产阶级财富的特定性质,这正是由于在他看来资产阶级财富是一般财富的最适当形式。因此,在经济上,虽然从交换价值出发,但是交换的特定经济形式本身在他的经济学中不起作用,他所谈的始终只是劳动和土地的总产品在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似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财富只涉及使用价值,而交换价值似乎只是一种礼仪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李嘉图那里就像货币周围流通手段消失在交换中一样消失了。因此,为了表明经济学的真正规律的作用,李嘉图也喜欢把这种货币关系看作只是形式的东西。由此就产生了他的货币理论本身的弱点”(同上书,第292—293页。黑体为原著者加)。斯密、李嘉图看不到资本与劳动之矛盾对立、之剥削压迫的阶级性质,当然也就看不到,在资本与劳动之间所发生的所谓自由交换中的自由,就只能是形式上的自由而非实质上的自由。
[8]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1页。黑体为引者加。
[9]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1页。黑体为引者加。
[10]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2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1]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2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2]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3页。黑体为引者加。
[13]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3页。
[14]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4页。黑体为引者加。这说明早在一个半世纪前,高瞻远瞩的马克思,就已经是揭露和批判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的伟大先知了。
[15]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00—10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6]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7]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7—108页。黑体为引者加。
[18]马克思说,追加资本作为“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无酬的他人劳动产生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2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黑体为引者加。
[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205页。黑体为引者加。
[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24]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关于“虚幻共同体”与“真实共同体”的许多精深论述,实际上是关于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的一个批判性阐述。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之阶级本质的揭露是如此深刻,但我依然钟情于黑格尔关于国家作为市民社会之真理形态的理性国家观,这一信念自1980年初读《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始就一直挥之不去。随着现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特别是在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作为“普照的光”越来越洒遍当代中国大地的今天,我对黑格尔国家观的合理性愈加笃信不疑。
[25]存在于马克思资本哲学中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在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中却转变为两者的抽象对峙和绝对对立,形式自由的维度在社会革命的历史激流中成为理论盲点和实践盲点,形式自由的维度所本来具有的历史性价值,就因此而全面沦陷在实质不平等不自由之抽象批判话语的汪洋大海之中。
[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黑体为引者加。
[27]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15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5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7—928页。黑体为引者加。
[3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黑体为引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