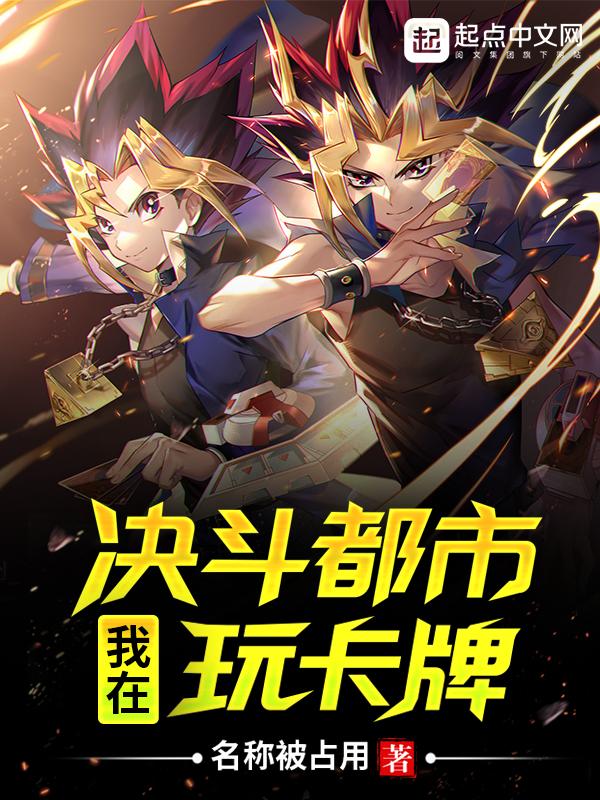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西方美学史 第1卷 古希腊罗马美学 > 第二节 美的本质(第2页)
第二节 美的本质(第2页)
就普洛丁而言,他尽管肯定“美主要是诉诸视觉”,实际上却认为,是由于灵魂中所固有的美,才使可感的事物显示为美:
首先应该肯定:美就是善,心智从善那里直接取得它的美;灵魂也因心智而美,其余如行为和事业之类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灵魂所授予它们的形式;而物体之所以能称为美,也是灵魂所使然。因为灵魂既然是一种神圣的东西,而且是美的一部分,凡是它所能控制和统辖的一切东西,灵魂都使之美乎其美,尽可能分有美。[46]
这里普洛丁从根本上即从三一原初原理上来说明感性事物和行为、事业之类的事物之所以美,都取决于第三原理灵魂的美,而作为第三原理的灵魂的美则相继派生自第二原理心智和第一原理善(太一、神),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善。雕像和建筑物所由以构成的质料石头等本身无所谓美,而是由分有美的灵魂将这种美作为形式,赋予作为质料的石头,这样才构成美的雕像或美的建筑,乃至美的行为或美的事业等。这里表明普洛丁既肯定感性美,又肯定知性美,但这两类美都取决于最终来自第一原理善的灵魂的美。这是他的审美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一般来讲,希腊罗马流行的美的概念,既包括感性美又包括知性美,柏拉图只肯定知性美或理性美,而希腊化时期的美学家只注重感性美。而普洛丁则正如塔塔科维兹所指出的那样:
普洛丁和两者都不同,他在美中看到了感性世界的属性,而这个感性世界却呈现了心智世界。形体是美的,但其之所以美是由于精神。换言之,感性世界是美的,但它的美来自美的理想原型。再者,外形式是美的,但其美的根源在于内形式。如果建筑物没有出现于建筑师的心灵中,它就不会有美的外形。新柏拉图主义美学家断定外部形状、匀称与和谐是美的,但认为这种美是借来的美,它“分有”内在的、精神的、心智的和理想的形式。[47]
的确,普洛丁并不否认感性美,并不否认某些感性事物的美与匀称的联系,即与比例等有关,但这只是美呈现自身的表现形态而不是美的本质。美的本质和根源不是匀称,而是呈现自身于匀称中的东西,即那种“光照”匀称的东西。他认为美在于统一,而事物中没有统一性,所以物质不是美的根源,所以美的根源只能是精神。美根本不是形态,不是色彩或巨大的体积,而是灵魂。普洛丁作为一个先验论者,强调灵魂的愉悦是极其自然的。通过色彩和形状等感性现象使人们感到愉悦,也是取决于灵魂的。所以感性美归根结底取决于灵魂,感性美只是起到提醒对灵魂中固有的美的理念(形式)的回忆而已:
至于各种最高的美,就不是视觉所能见到的,而是要灵魂不凭借感官去观照它、去判断它,在观照时,灵魂升到上界,把感觉留在下界。[48]
这种凭借灵魂的美去观照由灵魂赋予外在事物中的美,实际上是同一种美,更进一步讲也就是灵魂主体的美和灵魂外化了的客体的美的同一:“必须使视觉主体近似或符合于视觉对象之后才能够观照,如果眼睛还没有变得合乎太阳,它就看不见太阳;如果灵魂还没有变得美,它就看不见美。所以,无论何人,如果有心要观照神和美,都要首先肯定自己是神圣的和美的。”[49]这实际上是主体灵魂的自我认识、自我同一而已。美是属于作为主体的灵魂所固有的,可感事物之所以为美,是由主体的灵魂(如艺术家或建筑家的灵魂)赋予(用当前人们熟悉的语词是“外化”)外物的形式;当主体的感官看到、感觉到感性事物的美时,就观照到感性事物中的内在美(即美的形式、美的理念),这种内在美是灵魂所赋予的。所以主体的美和客体的美都是属于灵魂的美,都是灵魂所固有的。
四美在于分有理念
柏拉图在其中期的著作《斐多篇》、《会饮篇》、《国家篇》中,在讨论到可感的美或善的事物时,认为它们的美或善是取决于可知的美理念或善理念。他的论证过程是先设定一个最强的逻各斯,即原理或原则,和它相符合的才是真的。这个逻各斯便是肯定绝对的美自身(美理念)或善自身(善理念)等的存在。其他美的事物之所以是美的,是由于美理念,美理念是一切美的事物之所以是美的唯一真正的原因。反之,如果说美的颜色或美的形状等是造成事物之所以为美的原因,只能导致混乱。所以柏拉图认为,只是由于美理念,一切美的事物才成为美的。普洛丁也持相类似的观点。他声称,美的事物之所以成为美,取决于美理念:“一切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理念,而理念是由心智的本质产生的。”[50]
既然肯定美的事物(“多”)取决于美理念(“一”),这里就出现“多”和“一”的关系问题,即“多”和“一”的结合问题。柏拉图凭借“分有”来解决这个问题,认为美的事物之所以成为美是由于分有美理念。普洛丁也同样如此,他在《九章集》第一集第六章第二节中,结合回忆说,阐述的观点,也认为感性事物之所以美,取决于所分有的理念(形式):
话转回来,让我们首先谈谈原初的美到底是什么。它是第一眼就可以感觉到的某种东西,灵魂仿佛有所理解,就断定它美,认识了便欢迎它,宛若情投意合。但是,遇到丑的东西,灵魂便悸动不安,拒绝它,摈弃它,视若不相投契、异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说,灵魂既然是灵魂,而且最接近于比它更高的真实界,所以一旦见到自己的同类或同类的踪迹,便为之惊喜若狂,去亲近它,因而回想到自己和自己的一切。那么,此岸的美与彼岸的美有什么相似?因为如果是相似,就是相似罢了。为什么两者都是美呢?我们说,这是因为它们分有了形式。因为凡是无形式而本该取得一种形式或形成的力量,在没有分有得形成的力量或形式时,还是丑的,与神圣的形成的力量不相容的。而这就是绝对丑。此外,凡是未由一种形式或形成的力量统辖着的东西,因为它的物质尚未完全按照形式而形成,它也是丑的。[51]
这段阐明分有说的言论具有丰富内容。首先,灵魂在感官的启示下(“第一眼”)感觉到美的物体,就能回忆起(“有所理解”)灵魂中固有的美的形式(理念),从而断定由感觉引起的美的物体是美的,所以“为之惊喜若狂”,彼此“情投意合”。但要是灵魂感受到的是异己的丑的物体,由于灵魂并无丑的形式(理会),所以灵魂便排斥这种丑的东西,灵魂对丑的东西感到“悸动不安”,从而要摈弃它。其次,通过灵魂的这种“有所理解”,即达到心智领域,便认识到“此岸的美”(指可感事物的美、可感世界的美)与“彼岸世界”(指可知事物的美、可知世界的美),两者不仅相似而且都是美。这是由于可感事物分有了“彼岸世界”的美的形式(理念),所以成其为是美的,即“此岸世界”的美,来自“分有”“彼岸世界”的美,可感世界之所以美,由于“分有”可知理念世界的美,所以两者不仅相似而且都是美。否则便是丑的。最后,灵魂在“此岸的美”和“彼岸的美”之间起到至关紧要的中介作用。前面已从本体论上阐明过,艺术家由于将美的形式赋予作为质料的石头,所以创制出来的雕像是美的,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分有”,石头经过艺术家的创制从而分有了美的形式。这里还从认识论上来阐明这点,灵魂中是固有着美的理念的,当灵魂感知到“情投意合”的可感对象,便会“有所理解”,从而“回想到自己和自己的一切”,其中当然包括“回想到”“美理念”,就进而理解到所感知的物体是美的。反之,要是灵魂所感知到的是“异己的东西”,那灵魂就无从“回想到自己和自己的一切”,因而所感知到的便是丑的东西。“此岸的美”与“彼岸的美”,无论是在本体论上还是在认识论,都是凭借灵魂的中介作用才得以体现的。这种中介作用是由灵魂所特有的两重性带来的,因为灵魂既与可感世界相联系,又与可知的心智世界相联系。
至此,普洛丁以“分有”说来说明美的事物之所以为美,与柏拉图的“分有”说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在进一步具体解释事物如何分有美的形式(理念)从而成为美的事物时,这位持“动力学的泛神论”[52]的普洛丁,便与他极度崇敬的柏拉图有所分歧,从而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来申述分有说。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永恒静止不动、不变的,是与由其派生的可感世界相分离的,既然这样,用分有说无法解释这两个彼此分离的世界的结合。这点正像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六章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十个论证中“尤其重要”的第七个论证所揭示的那样:如果理念和具体可感事物是分离的,这样虽然肯定了理念,对于现实世界(即普洛丁所讲的“此岸世界”)中的具体事物,无论是关于它们的运动、认识或是存在,都是无济于事的。也就是说,柏拉图的理念本身是静止不动的,因而不具备动力因,无法使理念和被分有的具体可感事物相结合起来,亚里士多德因而提出四因说来取代它。普洛丁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这里就将“形式”(“理念”,一般中译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柏拉图的“理念”,来自同一个希腊语词“eidos”)理解为“形成的力量”,兼具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以此来说明美的理念如何将美赋予被分有的物体,从而使物体成为美的。
于是,形式到来了,把一件由许多部分组成的东西加以组织安排,使之成为一个秩序井然的统一体,于是创造了一个和谐统一的东西,因为形式本身是统一的,而那因形式而取得形状的东西,在杂多所能够成为统一的范围内,也应该是统一的。所以一旦结合为整一体,美就安坐在它上面,使得它的各部分和全体都美。但是,当形式落到一个统一而且均匀的东西上面时,它就以美授给了整体。这仿佛是大自然独运匠心,把美有时授予整个大厦和它的各部分,有时却授予一块砖石。由此可见,物体美是因分有了一种来自神明形式的形成力量而产生的。[53]
普洛丁这里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式来重新解释柏拉图的分有说。这里的形式已不是柏拉图所使用的意义上的静止不动的理念,而是能对质料、物体起到“组织安排”作用的“形成的力量”,它对于质料、物体而言,是在先的、现实的、能动的积极的力量或运动的源泉。而构成事物的质料、物体,如构成铜像的铜、构成人体的肌肉和骨头等,则是消极的、被动的、潜在的,不具统一性或整一性,自身没有运动能力,所以不能自行改变潜在状态。正是构成美的雕像所以美的形式、构成大厦所以美的形式,具有使它们成为统一、整一的“形成的力量”,“授予”作为质料的砖石,从而创制美的雕像或美的大厦。
就同样是唯心主义的范围而言,普洛丁这里吸收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形式质料说,重新解释柏拉图的以《斐多篇》为代表的分有说,确是将辩证的、能动的因素灌注到分有说中。雕刻家在从事雕塑时,建筑师在从事建筑时,在头脑中的确先有塑像的观念、建筑物的设计,这正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特点所在。蜜蜂在构筑蜂巢前不可能先有蜂巢的观念,纯粹是凭借本能进行操作的。问题是,这种先行的观念(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和普洛丁的形式)并非是天赋的,不是从事创制的雕塑家和建筑师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人类在从事雕刻和建筑的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而且到底雕塑什么样的雕像,营建什么样的建筑,还受到雕塑家和建筑师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其他种种物质条件和文化背景等复杂因素的影响。
五真、善、美的统一
普洛丁同样也热衷于追求和论证真、善、美的统一,他在多篇论文中,从各个侧面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里将它们汇集在一起进行申述。至于类似柏拉图那样在《会饮篇》中的论证,我们放在本章第四节讨论。
首先,美流溢自太一(善),因此美与真和善有同样的尊严。
普洛丁在其编年程序中的第三十八篇论文《理想—形式的多样性如何成为存在:论善》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普洛丁声称,太一的美是独一无二的,它是高于一切美的一种美:太一不能说就是美,因为太一不是各种事物中的一种事物。太一是可爱的,是美的创始者,它对一切美的形状来讲是这样一种力量,是美的顶点、终极,使一切成为可爱的。“太一降生美,并使美变得更美,因为这种美是由于美的过度而自太一中流溢出来的,太一是美的源泉和顶点。太一作为美的源泉,使无论什么样的美都产生自太一。”[54]由太一授予的美本身是没有形状的,而是分有这种美的东西才有形状。
由此可见,普洛丁强调的是美与最高原理太一的统一,因为这种美是从太一流溢出来的,由于太一本身的美的过度,盈则溢而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的。这种流溢自太一的美是无声、无色、无形的,也就是美的形式(理念),只有分有这种美的形式的分有者才是有形状的,因为后者是美的形式和质料的结合体。
其次,美与存在是统一的。
普洛丁认为,此岸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是自生自灭的,而彼岸世界[55]的能力却不然,它只有存在,只有美。因为在心智世界中美与存在是同一的、统一的,所以不可能有失掉存在的美、没有失掉美的存在。“因此,存在之所以可欲,正因为存在就是美,美之所以可爱,正因为美就是存在。”[56]就艺术作品而言,它是种虚构的存在,它必须反映外来的美,才能显得是美而获得存在,它只有分有理念的美才显得美,分有的理念愈多就愈显得完美,而且愈接近美的本质。
由此可见,普洛丁肯定在彼岸心智世界(即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美与存在是同一的。作为模仿的艺术作品,原本是虚构的存在,所以谈不到美也谈不到存在,只有当它分有美理念,才显得美才取得存在。
再次,美凭借爱和善相统一。
普洛丁并不否认美与匀称之间的相互联系,但他否认匀称就是美的本质,声称美能展示为匀称,但美不就是匀称本身,美是能真正激起爱的东西。这样他就通过这种爱,将审美中的美和伦理中的善相联系、相统一起来。重视爱、爱情、爱神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在这点上普洛丁是与柏拉图一致的。
普洛丁在进行辩驳匀称不是美的本质时指出,一个人的面容生前死后都“保持完整和匀称”,但活着时的美更加光耀,而死后却惨淡无光。循此,最逼真的肖像最美,尽管其他肖像更为匀称。活着的丑人,比雕塑的美人像更有吸引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活人有灵魂、有生命力,有更多的善理念,能行善:
这是因为他更加接近我们寻求的对象,之所以说他更接近是因为他有灵魂,有更多的善的理念,有善的光辉,这一光辉唤醒并激励着灵魂和灵魂所支配的一切,把他争取到善行上来,使他充满着无限的生命力。[57]
最后,真、善、美统一于净化的灵魂和神。
普洛丁在讨论到德性的美和知识的美时讲到,各种最高的美,不是凭借视觉所能见到的,而是凭借灵魂的凝神观照才能把握到的。正是在这种凝神观照的过程中,灵魂上升到上界彼岸世界,从而能判定事业的美,只有欣然爱事业、爱知识一类的美,即爱作为真知的美,才能判定德性的美、德性的光辉。灵魂一旦观照到了事业、知识一类的美,比之感觉到物体美就更有强烈的喜悦、惊愕、兴奋,“因为我们现在把握的是真正实在的美”[58]。
普洛丁进而申述,这种“真正实在的美”,只有凭爱和灵魂的净化才能把握到。他所要探讨的并非是对感性事物的爱,而是对美的事业、美的性格、德性和灵魂方面的美的爱,对神圣的知性的光辉的爱。因为只有这些才是“真正实在的美”。要达到这点,灵魂就需要净化。由于当灵魂进入肉体时就变得污浊,处处都堕入感性事物的陷阱,染上了许多肉体方面的杂质,甘心与许多物质性方面的东西合在一起,吸收了异己的理念(形式),从而蜕化变质。这就像一个人陷在污沼泥浆中,显不出他原有的美。所以这种被沾污了的灵魂就要净化:“只有在净化了由于和肉体结合得太紧而从肉体染来的种种欲望,摆脱了其他情欲,洗净了因物质化而来的杂质,还纯抱素之后,灵魂才能抛掉一切从异己的自然中得来的丑。”[59]
普洛丁进而申述,只有净化了的灵魂才能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就是统一于神。当灵魂一旦得到净化就成为理念(形式)和“形成的力量”,灵魂也就变为无形体的,也就纯然属于心智的。这是由于,灵魂一旦得到净化后,就被提升到第二原理心智,其美也随之增加。当灵魂变得善和美时,也就变得像神一样,真、善、美也就是一回事:
或者毋宁说是,美就是实在(即真——引者),其他非实在的东西是丑,同时也就是原初的恶。因此,对神来讲,善和美的性质是相同的,或者,实在、善和美是一回事。[60]
这里,普洛丁以灵魂的净化来讨论真、善、美的统一。灵魂一旦得到净化,它就摆脱了肉体的羁绊,它也就进入第二原理心智领域,心智领域也就是理念世界,其中当然包括美理念,而第二原理来自第一原理善。正因为这样,在净化了的灵魂中真、善、美是统一的。实质上是凭借三一原初原理的统一来论证真、善、美的统一。第三原理灵魂流溢自第二原理心智,第二原理心智流溢自第一原理善,所以既然三一原初原理三者本身是统一的,随之而来真、善、美也必然是统一的。
因为,归根结底真、善、美三者最终都来自神(太一、善)。尽管有太一、心智、灵魂等三一原初原理,但是万物一源,三者始终保持着同一性,第二原理心智、第三原理灵魂都出自第一原理神。它们彼此的关系是,离太一越远就越不完善;但不多不少只需这三个原初原理,太一是终极最高原理,它也就是神、善;心智按其本性是处于永恒的活动之中,向着和围绕心智运动的就是灵魂的活动。从心智向灵魂过渡,就使灵魂具有思想的力量,在心智和灵魂之间是没有任何东西插入的。思维并非是一种杂多的东西,它是单纯的,真正的心智就是在进行思维活动的思维,它所思的对象不在它自身以外而就是它自身,自身就是它所思的对象。灵魂是从心智流溢出来的,它是心智的形相,上焉者高等级的灵魂实际上是属于心智领域,下焉者低等级的灵魂已进入有形体的可感现象世界。因此,太一、心智、灵魂虽说是三个领域,但实际上是统一体,类似来自同一个同心圆的流溢、喷射、辐射、散发、光照。[61]
既然作为第三原理的灵魂是从第二原理心智流溢出来的,因此它潜在地就具有心智的一切特征,特别是高等级的灵魂,它具有记忆、回忆、想象等功能,凭借视觉在可感事物的作用下,凭回忆和推理可以重新回忆灵魂所固有的美、善(作为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善,而不是太一意义上的善)等理念(形式)。这时的灵魂实际上已进入第二原理心智领域,而心智的内容是有生命的存在、数、理念(美理念即属于这个领域)。所以普洛丁的心智领域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而理念世界派生自终极最高善理念(本体意义上的善)。普洛丁循此,认为心智第二原理派生自第一原理太一(善、神),所以高等级灵魂所固有的美理念,既是属于它所流溢自的心智领域,又是间接地属于心智所流溢自的第一原理善。所以从根本上讲真、善、美始终是统一的,只是由于灵魂进入人的肉体遭致可感世界的玷污,才丧失了这种统一,以后经过净化重返太一,才能重新恢复这种统一。这点正是普洛丁重视美学理论,也正是他制定整个体系所追求的主要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