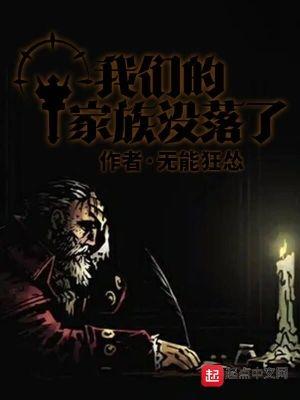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走奉天 > 打更老人死街角 老马猴子闯民宅(第1页)
打更老人死街角 老马猴子闯民宅(第1页)
早春的东北,仍然凛冽非常,早春东北的夜,更是如同墨汁浸透的棉絮,沉甸甸地坠在奉天城的头顶,漫天星斗镶嵌在乌压压的云层之中。
几盏昏黄的灯光浮在街角,映出泥土地面上血污般的冰凌,泛着诡异的光。
巷子深处有一道人影正贴在土墙根游荡,那道人影身量极高,佝偻着厚厚的背。
它裹着一件灰扑扑的粗布袄子,袖口和领口磨得发亮,头上缠着一张褪了色的蓝布头巾,俨然一副妇人模样。
但当那人走近,脖颈上覆着的那层黑褐色绒毛便无处遁形。
在微弱的灯光中,它走得极轻,双脚落地没有半点声响,只有袖口处偶然露出的手指,在触碰到冰冷时略微蜷缩,这双手乌青乌青的,像野兽的利爪。
这就是老马猴子,专门吃不爱睡觉的小孩儿的怪物。
它停在一扇旧纸糊的窗前,硕大的脸紧贴微弱的灯光,肥大的鼻翼贪婪地翕动着,尽情捕捉着空气中孩童的气息。
窗纸随风微微颤动,屋内传来窸窸窣窣的说话声,几个孩子还在玩闹。
老马猴子枯瘦的手指搭上窗沿,“吱呀——”一声刺耳的响动后,铁片和木头一齐嘶鸣。
它缓缓俯下身,一张布满褶皱的脸上漆黑的眼窝死死盯着尚未入眠的孩子,嘴角咧上后脑,一排尖牙上还有残存的血渍。
老人们说,它就住在城外西北角的一座深山中,那是一处巨大的洞穴,洞壁上渗着墨色的粘液,洞里还有一个不见底的深坑,坑底堆着密密麻麻的小孩尸骨,白花花的骨头架子堆成了小山,洞里常年散发着腐臭的腥气,无数怨童的呼喊声萦绕在洞内,百年不散。
“。。。。。。就这样,老马猴子一看见没睡觉的娃娃,就会在半夜偷偷撬开门对着屋里放一个屁,把大人熏晕了以后,就摸黑把小孩叼走。。。。。。赶紧睡觉,不然老马猴子可就来吃你们了。”
热乎的炕头上,母亲的声音压得极低,配合着呼号的冷风,平添诡谲之感。
炕上铺着几床破旧但干净的被子,里面缩着三个孩子,大的这个十岁出头,小一点的五六岁,最小的还在襁褓,三个孩子脸蛋红扑扑的,听到母亲的故事后,大的两个吓得“嗷”一声钻进被窝,脚都不敢伸到底,连呼吸都不敢大声,生怕一个不小心引来杀身之祸。
母亲看着孩子们囧囧的模样,微笑着吹了手边的油灯,火苗轻轻抖了一下就“噗”地灭了。
不多时,屋里众人逐渐平缓了呼吸,恐惧让孩子们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他们一个个在梦里紧皱眉头,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梦外追到了梦中。
在一切都陷入平静之时,呼吸声变得非常清晰,屋门“吱呀”一声开了一道缝隙,一股黄绿色的烟雾随着冷气一道悄无声息地钻了进来,恶臭非常,孩子母亲轻咳了几声,便随着烟雾蔓延开来时,沉沉睡去。
片刻后,烟雾退散,屋门轻轻一掩,缝隙消失,光亮也随之湮灭,只是炕上最小的身影已然不见踪迹,空留下一团被子,残留着的体温也逐渐渗走,可怜的母亲却毫无意识。
“哐——哐——”,打更锣的声音响彻街道,撞在冰冷的砖墙上,反复回弹。
“三更子夜,平安无事——”苍老沙哑的男声带着疲惫,在街角响起,打更老人慢悠悠地走着,手上的破铜锣时不时敲动几下,破旧的棉布鞋踩在街面的冰晶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他尽力缩着脖子,两只手插在破袄袖子里,狗皮帽子下一股股白气在眼前凝结成冰霜,模糊了视线。
转过街角,他忽然瞥见前方阴影中站着一个高个女人,那女人身形佝偻,头上裹着厚厚的方巾,脸遮得严严实实,怀里鼓鼓囊囊的,像是抱着什么东西,隐约间像一个长满黑毛的球体,再擦眼一瞧,是一个婴儿的头颅。
“姑娘,这么晚了,怎么还抱孩子上街啊?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奉天人都热心肠,见对方是女人而且孤身一人,便好心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只是打更老人脚步刚一靠近,那女人忽然把头一转,露出头巾下的脸,那分明不是人脸,而是一张布满皱纹和黑褐色绒毛的兽面,一双猩红的眼睛在暗夜中尤其明显,像是两团鬼火。
老人吓得浑身瞬间僵直,瞳孔陡然一缩,喉咙中发出“额额”的声响,像是哽住了一般。
一口气没有喘上来,就“哐当”倒地,破锣也掉到地上轱辘老远。
天蒙蒙发亮,东方天际渗出一丝惨白的光,四平街上那个卖包子的王二挑着挑子正往店铺赶去,他走得匆忙,脚步踩在冰路面上,“咯吱咯吱”作响。
转过街角,他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踉跄着差点摔个狗啃泥:“你大爷的,什么玩意儿?”
他骂骂咧咧地朝后弯腰一看,这一看不要紧,吓得他魂飞魄散。
地上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正是昨晚打更的李老头。他浑身僵直,硬挺挺地躺在那里,头朝下,最骇人的是那张脸,血肉模糊,五官已经辨认不清,像是被什么东西硬生生剥下来,露出里面猩红的血肉和白森森的骨头茬子,血流了一大摊,渗进白色的冰晶里,扎眼得很。
“死人了,死人了!快来人啊!”王二连滚带爬后退几步,大喊道,他声音中带着哭腔,刺破凌晨的宁静。
不多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章斯年带着陈小四和其他两个警员匆匆赶来。
“都让一让,站到警戒以外,不要靠近!”陈小四声音清亮,带着威严,一边指挥秩序,一边给章斯年拦出一道路直通尸体。
围观群众越聚越多,议论纷纷,声音中透露着不安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