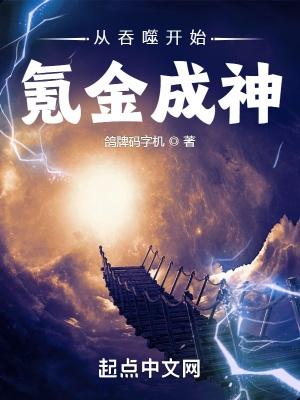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那年华娱 > 第一千四百九十四章 重返好莱坞力捧(第1页)
第一千四百九十四章 重返好莱坞力捧(第1页)
连续两天时间,国内各大新闻平台,尤以央视、微博、头条为首,都在实时报道着大洋彼岸的决战。
那副地图上,随着计票的不断进行,红色和蓝色在针锋角力,你夺下一城,我掠下一地。
直至国内时间14号。。。
艺菲合上日记本,将它轻轻放在窗台上。阳光斜斜地切过纸页边缘,照亮了最后一行字的尾迹,仿佛那不是墨水写就,而是光本身刻下的印记。她没有再看第二眼,因为她知道,从今往后,每一个读到这些话的人,都会成为新的书写者。
她走出屋子,脚步轻得像一片落叶贴着地面滑行。村口的孩子们早已散去,只留下那台老式录音机孤零零地躺在石凳上,电池盖歪斜着,像是打了个哈欠还没合拢嘴。艺菲蹲下身,手指拂过机身斑驳的漆皮,忽然听见里面传出细微的杂音??不是磁带转动的声音,也不是电流的嘶鸣,而是一种低频的、近乎心跳的律动。
她愣了一下,随即意识到:这台机器已经不再只是播放工具了。它的内部元件早已被共感能量浸润,如同老槐树根须下的土壤,悄然转化成了某种介于机械与生命之间的存在。此刻,它正在“呼吸”。
她没关电源,也没收起来,只是把它留在原地,任风吹日晒。她相信,明天会有人来取走它,或许是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或许是个流浪的民谣歌手。无论谁带走它,那首歌都会继续传下去,甚至变得更完整。
傍晚时分,天空泛起淡淡的紫红色,云层如绸缎般铺展,却没有任何雷声或风势预兆。艺菲坐在门槛上剥豆子,动作缓慢而专注。每一颗豆荚裂开时发出的“啪”声,在她耳中都像是一次微型的共鸣实验。突然,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不急不缓,踏在湿润的泥土路上,带着一种奇异的节奏感。
她抬头望去,是一个陌生男人,穿着洗旧的工装裤,肩上扛着一把木吉他。他的脸被帽檐遮住大半,但走路的姿态让艺菲莫名觉得熟悉??那种左脚略拖、右脚发力的方式,像极了多年前在县城文化馆门口见过的一位街头艺人。
男人走到院前停下,摘下帽子,露出一张布满风霜却眼神清亮的脸。“你好,”他说,“我听说这里住着一位‘听声音的人’。”
艺菲点点头,指了指旁边的竹椅:“坐吧。”
男人坐下,把吉他放在膝上,却没有立刻弹奏。他望着天边渐暗的晚霞,沉默了几秒,才低声说:“我在西北一个戈壁小镇待了八年。那里一年刮十个月的风,人说话要用吼,不然听不见。可就在上周,我半夜醒来,听见沙丘在唱歌。”
艺菲的手停在半空,一颗青豆滚落在地。
“不是幻觉。”男人继续道,“那声音很低,像是大地深处传来的哼鸣,频率……和《回应之歌》的主调几乎一致。我去查了气象记录,那天晚上根本没有风速变化,也没有地震波。可全镇的人都听见了。老人说那是‘沙漠的梦话’,孩子说那是‘星星掉进沙子里的声音’。”
他抬起头,直视艺菲的眼睛:“我一路南下,每经过一个村庄、一座城市,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录‘奇怪的声音’??井底回响、瓦片热胀冷缩的噼啪、晾衣绳在风中的震颤……他们把这些发到网上,标签叫#我在听。你知道最离谱的是什么吗?”
艺菲轻轻摇头。
“这些声音拼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旋律片段。AI分析说,它不属于任何已知音乐体系,但它能让人平静,甚至治愈长期失眠。有医生用它做背景音,结果三十七名抑郁症患者中有二十九人在七天内出现了积极情绪波动。”
他顿了顿,声音微颤:“我们是不是……正在集体创造一首从未存在过的歌?”
艺菲久久未语。她看着院子里那只跛脚狐狸悄悄探出头,耳朵竖起,似乎也在倾听这场对话。良久,她轻声道:“不是‘正在’,是‘一直都在’。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歌唱,只是以前没人愿意听。”
男人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拨动琴弦,一段不成调的音符流淌而出。就在这瞬间,艺菲察觉到一丝异样??那音符的尾音微微上扬,竟与屋后老槐树叶片震动的频率产生了共振。树叶轻轻摇晃,拼出两个字:
**“接引。”**
她心头一震。
“你会写歌吗?”她忽然问。
男人一怔:“只会弹别人写的,自己……没敢试过。”
“现在可以试试。”她说,“不用谱子,不用技巧,就唱你现在心里最想说的事。”
男人犹豫片刻,深吸一口气,指尖缓缓划过琴弦。第一个音响起时,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那不是吉他的声音,更像是某种古老乐器的共鸣,浑厚、悠远,带着砂砾般的质感。
然后,他开口了。
歌词很简单,讲的是一个旅人穿越荒原,寻找一口传说中的泉。途中他遇见死寂的村落、干涸的河床、烧焦的树林,每一次想要放弃,耳边就会响起一声极轻的滴水声,像是来自地底,又像是来自记忆深处。最后,他在一片白骨堆旁跪下,泪水坠落,砸进沙土。那一刻,泉水真的涌了出来。
歌声落下,四周寂静如初。但艺菲清楚地看到,院子角落那棵透明的小树苗,枝叶微微闪烁,金色丝线缠绕得更密了些。而在百米外的老槐树冠中,一只从未出现过的蓝羽鸟悄然落下,张嘴发出一声清鸣,竟完美复现了歌曲的最后一句。
男人怔住了:“我没有教过任何人这首歌……它刚刚才诞生。”
“但它已经被听见了。”艺菲微笑,“不只是你,也不只是我。还有树、有狐、有鸟、有风。它们都是听众,也都是传唱者。”
夜色彻底降临,星辰再度浮现。这一次,天幕上的光带不再是单纯的连线,而是开始编织图案??有的像藤蔓攀爬,有的似河流蜿蜒,还有的形同人脸轮廓,温柔注视着大地。科学家后来称其为“共感拓扑结构”,认为这是群体意识在空间维度的可视化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