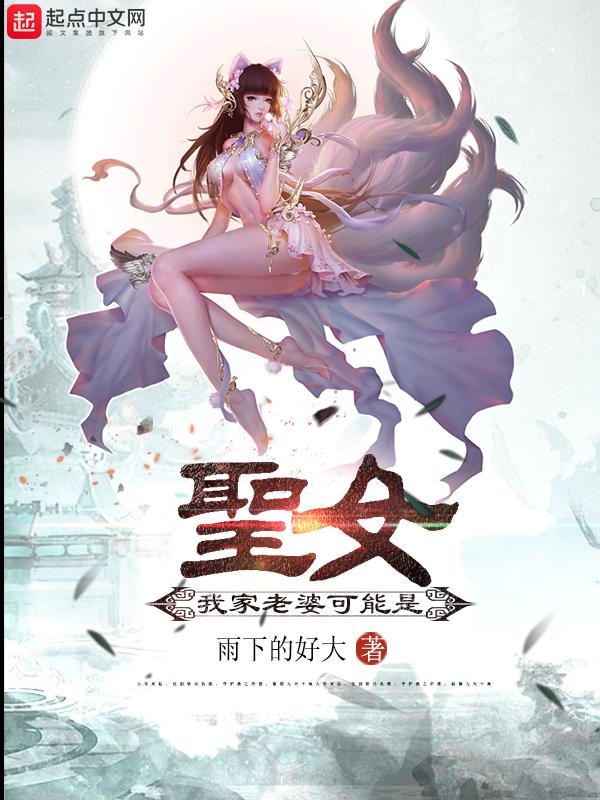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春色满棠 > 第497章 带他们相见(第1页)
第497章 带他们相见(第1页)
萧迟醒来,群臣振奋。
消息快速传去平叛的大军,平叛的大军此时已经跟叛军在襄城对上。
叛军占领了襄城。
朝廷平叛的大军想破襄城,平定叛军。
叛军则想突破朝廷大军,继续往京都方向打去。
故双方在襄城城外对战了几次,皆没有讨到便宜。
叛军每次见势头不妙,就退回襄城里,紧闭起城门,只防守。
而襄城固若金汤,想破城并非易事。
是以,双方一时僵持不下。
而在这紧要关头,一只小家伙来到平叛大军前,开口就说:“爷要见曹镇疆。。。。。。
暴雨过后的第七天,怒江水位终于退去。林小禾站在夜校门口,望着被冲垮的吊桥残骸横卧在浑浊江面上,像一道断裂的血脉。她手中攥着一封刚收到的信,纸页边缘已被雨水浸得发皱,字迹却依旧清晰??是陈佩兰从台北寄来的最后一封手书。
>“素心姐走的那年,海棠开得极盛。她说:‘若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和那些被遗忘的姐妹们一起刻进历史,我便死而无憾。’
>如今,我已老迈,看不清镜中的自己。可每当听见你们的消息,心里就像点了一盏灯。
>这次捐赠的手稿《女子心史》,是我十六岁那年躲在阁楼里一字一句抄下的。原稿早已焚毁于战火,唯有这份副本随我漂泊半生。
>请替我告诉所有还在寻找名字的人:你们不是孤身一人。
>我们曾一同哭泣,也终将一同看见春天。”
林小禾读完,指尖轻抚信纸,仿佛触到了半个世纪前那个蜷缩在阁楼角落的少女心跳。她缓缓抬头,望向远处山腰上那棵老海棠树??母亲埋下第一枚陶罐的地方。枝头嫩芽密布,如万千细小的手掌伸向天空。
苏晓踩着泥泞跑来,裤脚沾满草屑,“云南考古所刚确认了!桐木坪小学地下不止一个埋藏点,他们发现了第二批铁盒,年代标记为1968年秋。里面全是林素心老师当年组织妇女扫盲班时的学生作业本,还有她亲笔写的教学日记。”
林小禾闭上眼,呼吸微微颤抖。那是母亲人生中最艰难的十年。批斗、游街、剃阴阳头,她却仍偷偷办夜校,在煤油灯下教女人写字。有人问她为什么不怕,她只说:“字认得人,人就能活回来。”
“打开没有?”她低声问。
“没敢动。”苏晓摇头,“生物锁识别失败三次就会永久锁定。但……有一本练习册卡在裂缝里,被人抽出来过。上面有个名字被反复描黑??‘赵秀兰’。”
林小禾猛地睁眼。
这个名字,她们见过。
三年前,在广西边境一座废弃供销社的地窖中,发现过一具女性遗骨。身旁散落着半本识字课本,扉页写着“赵秀兰,19年生”。法医推断死亡时间约为1970年前后,死因系长期营养不良与外伤感染。而根据残存户籍资料,此人原为县文工团独唱演员,因拒绝嫁给某干部做妾,遭举报“作风问题”,逐出单位,流落山村。
当时,“她谱”团队耗时八个月才找到她的弟弟。老人接过姐姐照片时嚎啕大哭:“我们找她三十年啊!家里族谱早把她除名了,说她‘辱没门风’!”
而现在,这个名字竟出现在母亲的教学日记中?
“立刻调取影像备份。”林小禾声音冷峻,“我要知道是谁动了那个盒子。”
当晚,技术组还原出一段模糊监控画面:一名戴斗笠的男子深夜潜入封锁区,动作熟练地撬开土层。他并未带走核心芯片,而是特意抽出那本作业本,在“赵秀兰”三字上涂抹某种液体后迅速撤离。经检测,那竟是强酸??足以腐蚀纸质记录,却不触发防盗警报。
“这不是盗窃。”林小禾盯着屏幕,眼神锐利如刀,“这是清除。他们在系统性地抹去某些特定的名字。”
苏晓脸色发白:“可这些人早已死去,为何还要追杀记忆?”
“因为活着的人怕。”林小禾缓缓起身,“怕真相醒来,怕问责降临,怕那些被压在历史尘埃下的冤魂,一个个站出来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还记得吗?你做过什么?”
她拨通国家档案局专线,请求启动“百年女性声音复原工程”的紧急溯源程序。同时下令全国“时间信箱”守护站点升级防御等级,并通过“她谱”APP向百万学员发布特别通告: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参与过妇女扫盲、教育推广、文艺工作,请联系我们。
>每一份口述,都是对抗遗忘的子弹。
>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把打开正义之门的钥匙。”
消息发出不到十二小时,后台涌入两千余条线索。其中一条来自江苏盐城,署名“王阿娣之子陈国富”:
>“我妈是1965年县妇联派去农村教书的老师。她说那时候好多女人一辈子没名字,生了孩子就叫‘张大嫂’‘李二婶’。她坚持让每个学生写下真名,哪怕不会写,也要按手印。后来有人告密,说她‘煽动妇女闹独立’,她被关了两年。放出来时嗓子坏了,再也不能说话。去年她走了,临终前一直用手比划三个字??‘写下来’。我把她的教案本留着,能不能……也算一份‘她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