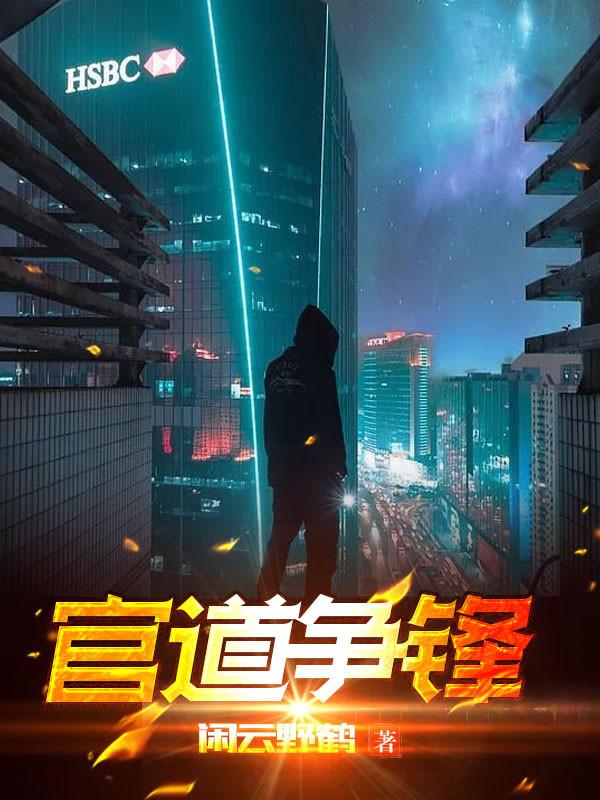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蜀汉之庄稼汉 > 第1465章 谈判(第4页)
第1465章 谈判(第4页)
有求于人的卑微,彻底剥夺了他讨价还价的资格。
还是那句话,国事是国事,私人关系是私人关系。
没必要因为为了国事,而去尝试触怒冯大司马,恶化私人关系,不值得。
半晌,秦博重新躬身,彻底放弃了挣扎:
“君侯……………思虑周全,安排妥当。博,谨遵君侯之意。一切,便依君侯所言办理,唯恳请君侯早日奏明陛下,解我荆州倒悬之急。”
“若换成别人,我未必会给这个面子,但既是秦君有求,那我明日一早就入宫,奏请陛下。”
“多谢君侯。”
“不须如此客气。”
正事既毕,气氛稍显缓和。冯永看似随意地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将话题引向了吴国近况:
“元逊诸葛恪字总揽大政已有些时日,如今建业城中,各方反应如何?”
秦博闻言,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复杂的苦笑。
他略一沉吟,便开口谈起大皇帝驾崩后的情况:
“回君侯,太傅甫一上任,便连下数道惊动朝野的政令。’
“首要之举,便是下令免除百姓积欠的赋税,并废除了各处苛扰商旅的征税关卡,此举民间称颂者甚众。”
冯永微微颔首,不置可否:“哦?看来元逊是广施德泽,以收民心。那。。。。。。校事呢?”
这才是他真正关心的重点,校事府是吴国与兴汉会贸易的关键渠道,而且还是自己扶植了十几年的钉子。
虽说早就收回成本,但谁嫌自己赚得多?
真要被诸葛恪一通乱拳干死,那才叫冤枉。
听到冯大司马问起,秦博的笑容更苦了几分:
“太傅曾有意裁撤校事府,认为其鹰犬之行有伤国体。后来。。。。。。后来一方面是朝中不少与之有旧者求情。”
他话语微顿,眼神复杂地看了冯永一眼。
听吕中书说,幸好有某位糜姓的先生,提前给校事府做了谋划,这才让事府逃过此难。
而那位先生,似乎又与眼前这位君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甚至有传闻,说是糜十一郎是直接听命于冯大司马。
怀着乱七八糟的心思,秦博继续说道:
“另一方面,太傅也是考虑到校事府多年来专司与大汉的交通贸易,颇建功勋,骤然裁撤,恐伤两国往来之利。太傅权衡再三,这才勉强同意保留。’
他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几分自嘲与无奈:
“不过,校事府如今已是今非昔比。太傅严令,日后不得再行监察官民之事,需专心经营‘平准司’职能,说白了,就是专为朝廷筹措钱粮。
“就连吕中书,也屡屡因旧日行径被太傅当众斥责,若非其赌咒发誓谨守本分,只怕性命难保。”
说着说着,秦博竟是带了几分情绪,就像是一个饱受委屈的旧朝遗老:
“君侯明鉴啊。。。。。。像下官这等昔日校事府老人,如今更是动辄得咎,稍有行差踏错,便是万劫不复。”
“此番出使,名为国事,实则。。。。。。唉,博也是被逼无奈。否则,博又岂会来君侯面前自讨无趣,惹得君侯生厌?”
“实则只做这苦差事,方能显得安分守己罢了。想当年。。。。。。唉!”
跑来跟巧言令色的冯鬼王谈判,还想着要从对方手里占便宜,这不是苦差事是什么?
这番诉苦,半是真心的感慨时局艰难,校事府地位一落千丈。
半是刻意示弱,希望能多多博得这位权臣的些许同情或体谅,为日后留下一线香火情分。
冯永静静地听着,目光深邃,让人看不出他心中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