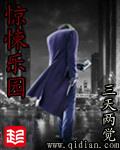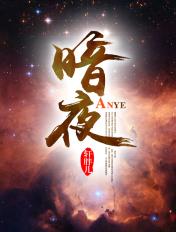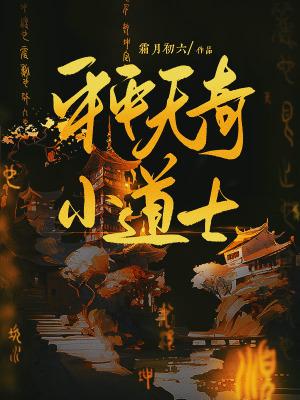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人间有剑 > 第四百五十四章 恩仇(第1页)
第四百五十四章 恩仇(第1页)
“道友此言何意?”
长草道人端着空碗,一脸疑惑。
年轻道士仰起头,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说道:“你可知道刚才那钟声从何而来?”
长草道人微微蹙眉,试探道:“不是来自天穹之上?从天外而来?”
“说是天穹之上倒也不算错,但却不是天外,在那天穹深处,有一座天宫,大真人居于此处,你难道不知?”
年轻道士看着他,只是微笑。
长草道人皱眉道:“贫道怎会不知道,那天宫大真人是我道门之主,世间万千修道之士,皆敬仰之!”
夜深了,祁连山的风穿过知语堂的窗缝,吹动墙上那幅《言剑》复刻版的一角。纸面微微颤动,像被无形的手指拂过。青年坐在桌前,手中握着一支旧钢笔,墨水瓶里泛着幽蓝的光??那是从云知遗物中找到的特制药水,据说能在黑暗中显影出被涂抹的文字。
他盯着留言簿最后一页上自己写下的那句话:“最渺小的真话,也比最宏大的谎言更有重量。”字迹已干,可心头却如潮水翻涌。他知道,这句话不是终点,而是一扇门,刚刚推开一条缝隙。
手机又震了一下。这次是周念发来的消息,只有短短一行:
>“《灰幕》第三版完成,准备送往十个城市同步放映。他们封得了网,封不了人眼。”
他回了个“好”字,放下手机,忽然听见屋外有脚步声。轻,缓,像是怕惊扰什么。他起身推门,见一个穿灰衣的女人站在梧桐树下,手里提着一只铁皮盒,面容隐在月影里。
“你是……?”他问。
女人抬起头,眼角有一道细长的疤。“我是赵立新的妹妹。”她说,声音沙哑,“我哥在狱中最后一年,常念叨一个叫‘知语堂’的地方。他说,如果有一天他的字还能见光,就送去那儿。”
她打开铁皮盒,里面是一叠用油纸包好的卡片,每张都密密麻麻写满铅笔字。编号从307到412,内容涉及九十年代初一场被掩盖的化工厂泄漏事故,受害者名单、赔偿金额、官员受贿记录,甚至还有当时记者如何被威胁删稿的细节。其中一张背面写着:“这不是证据,这是遗嘱。”
青年接过盒子,指尖微颤。“谢谢你送来。”
“谢我?”她冷笑一声,又很快收敛,“我不为他讨公道,他已经死了。我只是想让活着的人知道,有些人坐牢,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是因为他们不肯说谎。”
她说完转身要走,却被青年叫住。
“你哥哥……有没有留下一句话?哪怕一句?”
她停下脚步,没回头。“有。他说:‘别让我白坐了那十二年。’”
风停了片刻,仿佛天地都在默哀。
青年抱着铁皮盒回到屋里,将卡片一张张摊开晾晒,生怕潮湿让字迹消失。他忽然发现,在第389号卡片夹层里,藏着一小片烧焦的纸角,上面残存两个字:**云知**。
心猛地一沉。
他立刻拨通白发老太太的电话。铃响三声后,对方接起,声音疲惫却清醒。
“是我。”他说,“您还记得陈默的资料吗?刚才我发现赵立新的遗稿里出现了‘云知’的名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把卡片拍照传给我。”她说,“我今晚不睡了。”
凌晨两点,老太太回信。附件是一份扫描件,来自一份尘封的内部通报复印件,标题为《关于“言社”残余分子活动情况的紧急报告(1983年)》。文中提到:
>“据线人举报,原‘言社’成员云知,曾于1979年秘密联络多名异见知识分子,策划建立跨省信息传递网络,代号‘回声桥’。该网络旨在通过短波广播、手抄刊物及地下邮路传播未经审查之言论。主要联络人包括:甘肃教师陈默(代号‘回声’)、北京记者周振国(已自杀)、云南学生李文秀(失踪),以及一名化名‘守灯者’的图书管理员。”
文末附有一张模糊的手绘关系图,中间画着一朵铃兰花,象征云知;四周连线指向四人,其中三人已被标注“控制”或“死亡”,唯独“守灯者”一栏打了个问号,并注明:“疑为兰州图书馆某职工,尚未确认身份。”
青年盯着屏幕,呼吸渐重。
原来云知不是孤身一人。她曾试图点燃更多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