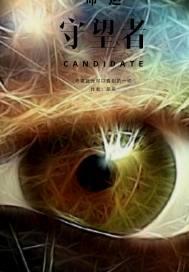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流民她青史留名 > 消息(第1页)
消息(第1页)
一场仗来得突然,耗时却不短,就这样从暮春打到了晚夏。
这期间,郊外的仁和书院分院已然建起来,军药作坊也得以扩建。
戎州府制出的伤药源源不断送向战场,各州前来仁和书院临时培训的军医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仍然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对战双方僵持不下,你来我往耗了一个又一个月。
吐蕃这回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倾尽全国之力,还带上数个周边附属的小国,似是孤注一掷,誓要从大夏撕下一块肉来。
敌众我寡,若不是有今非昔比的戎州军在前面压着,以其他几州的实力,只怕早已节节败退。
怎奈打了这么久,却始终不见朝廷派遣援军来。实在催得紧了,也就象征性地多发些军费粮草了事,仿佛已然顾不上这大夏西南方最重要的边境。
姜鹤羽想起曾在栗娘船上听到的那些商人的谈话,回忆着脑中还有印象的史料,算了算大概的时间,看向长安城的方向,眉间深深皱起。
只怕,是那向来病痛缠身的圣人,快到时候了。
她心事重重,也没怎么看路,一只脚刚踏进府衙门槛,就险些与匆匆而来的孟芸颖撞上。
小姑娘一个趔趄,好险稳住身形,正欲开骂,看清来人,当即又喜又急,拉着自家师傅的袖子大喊:“师傅!快!出大事了!楚王殿下要见您!”
“楚王?”姜鹤羽一怔,不明所以,“何时的消息?人在何处?”
“就是刚刚刺史府来信,说楚王殿下已经在路上了,师傅,您快准备准备。”孟芸颖紧张得出了一脑门子汗,手忙脚乱地失了方寸,“我也不知殿下突然来是要做什么,为何要见您,我……”
“天子也得讲王法,他还能吃了我不成。”姜鹤羽拍拍她的肩,带着她往值房去,“别急,你且慢慢说。”
孟芸颖这才咽了口唾沫,摸了摸发麻的胳膊:“好、好。”
姜鹤羽听她语无伦次地颠来倒去讲了半天,才弄明白,如今楚王殿下正在来戎州的路上,竟是跟在前来培训的新一批军医队伍中。
这位金尊玉贵的殿下不知抽的什么疯,像是一时兴起,也未提前传信,直到快到地方了才想起通知魏刺史,并且点名要见姜鹤羽。
这可将榻上瘫着左拥右抱的刺史大人吓得,一个咕噜爬起来,几乎是前后脚就将消息送到了医药司来。
姜鹤羽倒不如他们那般着急上火,面色平静地叩了叩茶盖。
其实她心里也拿不准这素未谋面的楚王意欲何为,但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位殿下并非什么为非作歹之人。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
。
三日后,府衙待客厅。
姜鹤羽垂首看着地上青砖,耳边只能听到上方茶盖缓缓磨在杯口的轻响。
如有实质的目光在她身上不知扫过多少次,直至一盏茶喝完,那人低沉的声音才在她头顶响起:
“抬起头来,本王看看。”
姜鹤羽领命抬起头,清凌凌的目光毫不避讳地直视上首之人。
端坐于蒲团上的楚王面宽耳阔,年逾四十,气宇轩昂,正值当打之年。
他身份贵重,是当今天子同父异母的弟弟,这样的出身,足以在史书上留下痕迹。
史载,成安二年,益州府城破,楚王李淏浴血杀贼百人,率家眷自焚于府中,只给闻风而来的敌军留下了一地残屋败瓦。
而前些时日,她曾听魏刺史偶然提起,天后殿下意在来年将年号从永嘉改为成安,以为圣人祈福。
姜鹤羽睫毛微颤。
楚王看着这个不卑不亢的年轻人,忽而不辨喜怒地赞了一声:
“胆儿挺大。”
“臣不敢。”姜鹤羽又垂下头。
“过来罢。”楚王摆摆手,示意姜鹤羽坐到他对面。
他提着宽大的袖摆,姿态风雅地给姜鹤羽重新沏了热茶,宛若一位文士,教人全然看不出他骨子里竟有那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血性。
“其实找你来也没什么紧要事。本王只是好奇得紧,想看看这军中吹得神乎其神的医药圣手,究竟长得什么三头六臂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