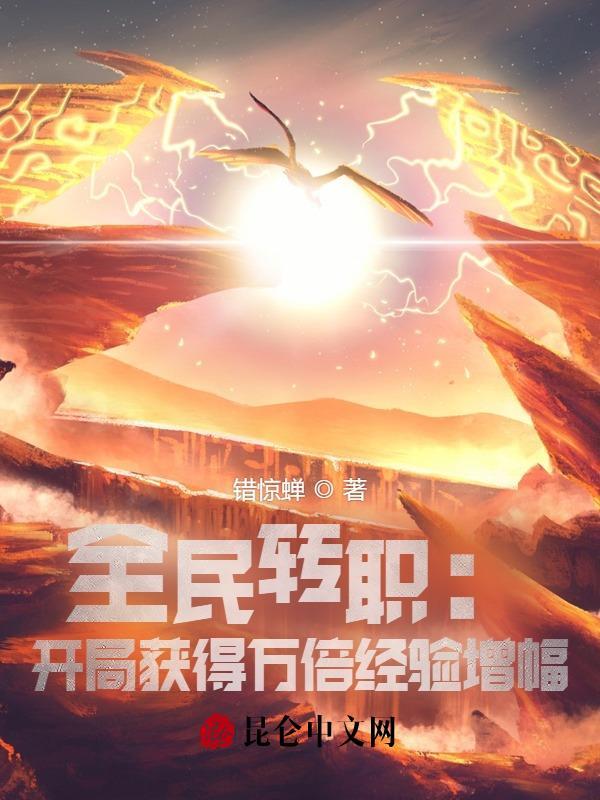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定夷 > 8090(第26页)
8090(第26页)
沈淙听明白了他的话,道:“说到底,父亲只是觉得现在和离对沈氏太亏了。”
“难道不是吗?宿幕赟在宋氏谋逆一案中有功,陛下一定会重用她,你不打一声招呼就去官府盖印,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还有沈氏吗?!”
“我也是个人,父亲,”沈淙看着他,说:“世家大族又如何?我不是物品,需要精打细算填在合适的位置上,需要送出去拿回来换取筹码,还要计较利益亏损,出入收支,我也有好恶,我也会伤心。”
“谁不是这样过来的——”沈蒲道:“难道我就没有好恶,不会伤心——”
“可我现在不想这么过了!”沈淙扬声打断他的话,道:“培养后辈成材,教以诗书道理,家族自会人才辈出,欣欣向荣,族中兴盛至今,难道是靠
姻亲而成的吗?长姐战功赫赫,你逼她留在晋州,阿济心有所属,你让他和那些从未见过面的人成亲,我——”
“啪——”
一个清脆的耳光打断了他的话,沈蒲冷眼看他,对着低头站在门口的仆从,道:“拿家法来!”
“不许去!”赶回家中的沈洵疾步迈入祠堂,上前两步掀袍跪地,道:“父亲息怒,阿淙和离这事是我同意的。”
沈蒲道:“你身为长姐,就这么纵容他?”
沈洵道:“不仅阿淙要和离,洵不日也要和离,望父亲同意。”
沈蒲不敢相信,问:“你说什么?”
“承平六年秋时,阿淙在晋州的一个酒楼中发现了密室,里面是南氏私开的赌坊,而这个酒楼的地契却在沈氏的手里,此事,父亲知道吗?”
沈蒲显然不知情,定定地看向她,说:“南焕卿竟敢?”
“父亲觉是南焕卿一人所为吗?”沈洵道:“我知道此事后,和阿淙一起将和南氏有关的产业全部查了一遍,里面有多少伪账就不说了,最可恨的是他们明明知晓中梁严禁世家私下经营赌坊、伎院等地,竟还用沈氏产业作伪为自己敛财,甚至还打着我和母亲的名号疏通关系。”
“当时时局纷乱,未免出事,我和阿淙并没有将此事捅开来,我想父亲也不愿,那如今悄无声息地和离就是最好的办法,这些地契直接还给他们,自可划清界限。”
沈蒲没想到自己为沈洵亲自选定的婚事竟会有如此内情,沉默几许,道:“南氏一事,我自会亲自查明,若此事属实你再和离也不迟,但你的事是你的事,阿淙的事是阿淙的事,他不仅先斩后奏,还忤逆长辈,我今日必须要动家法!”
“别动不动的就要动家法的,”门外又传来一个声音阻止了门边要离开的仆从,沈英迈步入内,道:“你以为小淙和你一样皮糙肉厚,几鞭子下去可得养一阵子伤。”
沈蒲见胞妹突然前来,便知是沈淙的主意,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既知道怕,当初又何必去做?”
沈英站在沈淙身边扶住了他肩头,示意他不用怕,道:“实话和你说吧,这事小淙早就和我说了,也是我为他写的文书,如今和离书已成,你再打再骂也无济于事,况且这些年小淙的辛苦你我都看在眼里,就算没有宿家又如何?”
沈蒲胸腔起伏,分外不解道:“婚事是能如此儿戏的吗?说和离就和离,他和我说了吗?和他母亲说了吗?和他祖母说了吗?如此目无尊长!”他指着沈淙,紧接着道:“我从小就是这么教你的?”
沈英道:“小淙从小就是这一辈孩子里最听话的那一个,他既决定和离,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你又何必如此生气。”
“那你让他说,什么理由,”沈蒲道:“他若是能说出个和他长姐一样的理由,我保证不生气。”
见在场几人的目光都望向自己,沈淙抿抿唇,道:“我就是想和离,没有理由。”
“拿家法来,”沈蒲懒得再和他拉扯,对着门口的仆从,道:“去!”
然还未等此人迈出一步,又有一人脚步匆匆地走了过来,站在门口道:“家主!”
“又怎么了?!”
那仆从显然没想到沈蒲火气正盛,吓得后退了一步,颤颤巍巍道:“将军、将军让我来告诉您,陛下来晋州了,现在正在边防营。”
此言一出,沈淙猛地回头看向了他,听见他继续道:“……贺将军得到消息,已经在路上了,将军就让我回家告知您。”
陛下两个字就像一盆冷水,将沈蒲的火气兜头浇灭了,他赶忙让沈洵起来,对一旁的沈淙道:“你继续跪着反省。”
“家主,”仆从又硬着头皮打断了他,说:“将军说,让您把二公子和三公子一起带上。”
那就是要见他们全家人了。
陛下微服私访,携全家见礼也是应该的,但如今沈淙这张脸……
沈蒲看着他脸上清晰可见的掌印,皱着眉道:“你先去收拾收拾,我会和陛下解释的。”
他迈步出门,随手指了指一个仆从,道:“你去叫三公子。”
吩咐罢,他又侧头看向沈洵,道:“阿洵,我们走。”
听着父亲和长姐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沈淙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只有自己一个人不被允许见谢定夷的场景,心中一片委屈,抬起指尖碰了碰自己的脸,发出一声低低的痛呼。
沈英皱着眉头看了看他的伤势,道:“起来,先去上点药。”
“我自己能行,姑母,”沈淙站起身,道:“多谢您今日来,我没事,我现在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沈英知道他心中委屈,但想了想,还是劝道:“其实这么多年,你父亲也不容易,他为家族和你母亲长姐的前程计,辞官归家,就是希望沈氏能偏安一隅,不要步一些世家盛极必衰的后尘……总之,不管他做什么,初衷也是为了你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