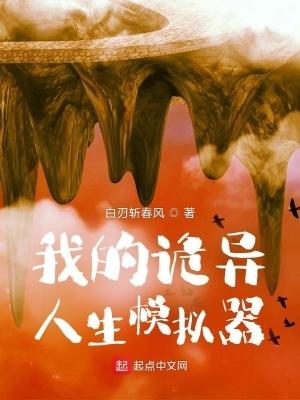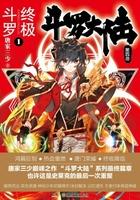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重生08:从山寨机开始崛起 > 第六百八十七章 财团之间的合作以及竞争(第2页)
第六百八十七章 财团之间的合作以及竞争(第2页)
陈默盯着屏幕上的波形图??微弱但规律的心跳曲线,在地图上闪烁如萤火。他忽然抓起通讯器:“接通那台设备,我要对他说话。”
频道接通瞬间,他深吸一口气,用最平稳的声音说道:“喂?听得见吗?我是陈默。你现在可能很冷,也可能很疼,但请相信,有人正在找你。你父亲救过的人,现在正跪在指挥部外求救援队再进一次山。他说,那条路是他答应替你爷爷走完的,不能断在这里。”
他顿了顿,声音微微发颤:“我也曾以为自己走不出黑暗。但我学会了,只要还有心跳,就不算结束。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整个‘倾听角’都在陪你等天亮。”
十分钟后,搜救队在塌方石堆下发现了三人。其中一名年轻护林员苏醒后第一句话是:“我听见了……有个声音告诉我,别睡过去。”
事后,巴特尔亲自送来一封蒙文写的感谢信,附带一双亲手缝制的皮靴。信中写道:“从前我以为守护这片山林是为了赎罪??因为我没能找到弟弟。但现在我知道,每一次伸手救人,都是在把丢失的声音找回来。”
春天彻底降临那天,“心语科技”举办了首场“无声发布会”。没有PPT,没有演讲稿,全场三百名观众戴上特制耳机,聆听来自全国各地的真实录音:
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反复念叨:“我记得我有个女儿,她最喜欢吃糖葫芦……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一名留守儿童对着空房间说:“爸爸,我在学校得了奖状,贴在墙上啦。你什么时候回来拍照?”
还有那个曾想跳楼的女孩,在倾诉亭里笑着说:“今天我主动跟同桌说了早安。她说,你的声音很好听。”
全场寂静无声,许多人低头抹泪。林远舟站在台侧,看着陈默缓缓起身,扶着助行架走向舞台中央。
他走得极慢,每一步都伴随着肌肉的颤抖与疼痛,但他没有停下。当他终于站定在聚光灯下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很多人问我,‘倾听角’到底改变了什么。”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会场,“我想说,它没让世界变得更聪明,也没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它让一些原本只能藏在心底的话,终于有了落地的声音。”
他停顿片刻,目光扫过人群:“我们总以为沟通是说话的能力,其实真正的沟通,是倾听的勇气。当你愿意蹲下来,听一个孩子哭,听一个老人唠叨,听一个陌生人说‘我很痛苦’??那一刻,你就成了光。”
发布会结束后,林远舟收到一条短信:父亲住院了。
他赶到医院时,老人正躺在病床上输液,脸色苍白,但神情平静。“没事,就是血压高了点。”他勉强笑了笑,“就是有点话,想趁还能说的时候告诉你。”
林远舟握住父亲的手,点点头。
“你小时候特别爱问问题,每天晚上都要听三个故事才肯睡。有一次你问我,‘爸爸,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我说,因为天上有人在跟我们打招呼。你信了,还非要说你也想当星星,照亮别人的路。”
老人喘了口气,继续道:“那时候我觉得你是胡闹。现在我才明白,你一直想做的,就是那个在黑暗里眨眼的人。”
泪水无声滑落,林远舟伏在床边,轻声道:“爸,我一直记得你说的那句话??鹰飞进来,是因为外面风太大。可我现在想告诉你,鹰之所以能飞,是因为它知道,总有一盏灯,会为它亮着。”
老人抬起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背。
与此同时,陈默正坐在康复中心的训练室里,完成当天的最后一组步行练习。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双腿如同灌铅般沉重,但他依旧咬牙前行。医生在一旁记录数据,惊讶地发现他的神经反射阈值正在稳步提升。
“照这个速度,三个月内,你或许可以尝试脱离辅助器械。”医生说。
陈默笑了笑,望向窗外盛开的樱花。“我已经不是为了走路而练了。”他说,“我是为了证明,有些看似不可能的事,只要有人愿意等,就会发生。”
当晚,“倾听角”推送了第1000万条用户录音:
>“我是个聋哑人。今天我去邮局寄信,工作人员看不懂我的手语,急得满头汗。这时旁边一个小女孩跑过来,用手语帮我翻译。她妈妈笑着说:‘宝贝,你怎么会这个?’她说:‘学校亭子里教的呀,老师说,每个人的声音都重要。’
>我抱着信站在阳光下哭了好久。原来我也能被听见。”
这条录音上线不到十二小时,转发量突破五百万。全国已有四十七个城市宣布将“匿名倾诉亭”纳入公共设施建设规划。教育部也正式批复,“情感教育课程”将作为试点项目进入中学课堂。
林远舟和陈默站在公司楼顶,看着城市灯火如星河铺展。
“你觉得我们做到了吗?”陈默问。
“哪一步?”林远舟反问。
“让世界多一点点温柔。”
林远舟笑了,仰头饮尽手中温热的茶。“我不知道世界有没有变温柔。但我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怕说出软弱,也不再羞于请求帮助。这就够了。”
夜风吹起他们的衣角,远处传来孩童嬉闹的笑声。在这个仍充满误解与隔阂的时代,总有一些人选择开口,也总有一些人选择倾听。
而正是这些微小的选择,像春天融雪渗入大地,悄然改变着坚硬的土壤。
某所中学的心理咨询室里,新安装的“倾听角”收到了一条清晨录音:
>“今天我要鼓起勇气,跟喜欢的人说早安。就算被拒绝,我也想让她知道,有个人,曾因为她而努力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