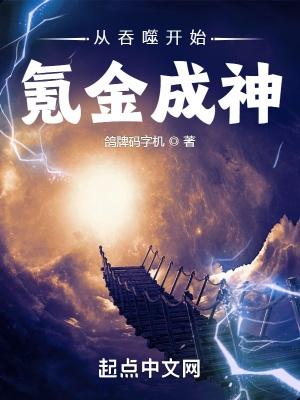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从现代归来的朱元璋 > 第三二六章 朱元璋交代给朱棣的任务(第3页)
第三二六章 朱元璋交代给朱棣的任务(第3页)
>今见尔等以科技为桥,以共感为路,终使沉默者得言,含冤者安息。朕心甚慰。
>然,警惕啊!
>技术可载道,亦可灭道。若人心复闭,纵有万棵晚星之树,亦不过朽木枯根。
>民怨不在书,不在碑,而在每日每夜,一人对另一人,是否肯俯身倾听。
>此即归途。
>此即重生。”
影像结束,屏幕渐暗。
控制室内,寂静如渊。
良久,林昭转身回到地下石室,重新拿起那支发丝笔,蘸水落墨。
他在宣纸上写下第一行字:
>“今天,我听见了朱元璋的忏悔。”
然后,他将纸放入木匣,合上盖子,命令工匠将其原样封存,并立碑于东华门前:
>“此处无物可掘,唯有心可鉴。
>凡欲知历史真相者,请先问自己:
>你,可曾真正听过身边人的哭泣?”
仪式结束后,林昭独自登上景山最高处。春风拂面,紫禁城全景尽收眼底。他掏出晚星的日记本,翻开最新一页,补写道:
>“晚星,树已扎根人心。
>朱元璋不是归来,而是从未离开。
>因为只要还有人愿意听,
>那些被掩埋的声音,
>就永远活着。”
夜幕降临,第一颗星星升起。
与此同时,全球七十二口“记忆之井”在同一时刻泛起微光,水面映出同一个倒影:一个布衣老人牵着小女孩的手,缓缓走入暮色深处。
没有人拍照,没有人录像。
但第二天,世界各地的孩子们不约而同画下了同一幅画。
画上题字稚嫩:
>“爷爷说,他是皇帝。
>可我觉得,他更像一个,
>终于能安心睡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