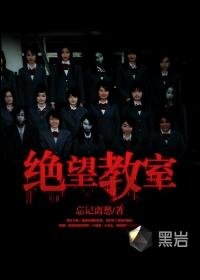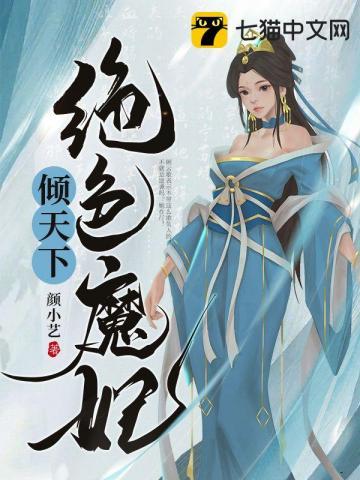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明末:我崇祯摆烂怎么了?! > 第344章 智计百出不违大势(第1页)
第344章 智计百出不违大势(第1页)
二十九日,潜入长岭山一带的奴骑再次现身,在宁远至塔山段袭击了明军辎重部队,焚毁粮草八千石,杀死明军辎重兵二百余,屠戮运粮和尚一千七百人。
次日中午,袁可立派遣支援的八百骑兵赶到,双方交战,明军竟。。。
晨光初透,乾清宫的琉璃瓦上泛起一层淡金。朱由检并未歇息,整夜伏案批阅各地奏报,眼下青黑如墨,却目光炯炯。王承恩端来参汤,战战兢兢道:“陛下已三日未眠,龙体要紧啊。”
“朕若睡了,那些人便要以为朕怕了。”朱由检冷笑,将一碗参汤一饮而尽,瓷碗重重搁在案上,“江南的火刚压下去,北疆又起风波,这时候谁敢合眼,谁就是死人。”
话音未落,殿外脚步急促,赵九渊再度入内,铠甲未卸,脸上犹带风霜之色。“启奏陛下!”他声音低沉,“昨夜密探自山海关急报:袁崇焕……被囚了。”
朱由检猛然站起,茶盏震翻,滚烫的汁液泼洒在龙袍前襟,他却浑然不觉。“你说什么?”
“蓟辽总督高第联合兵部尚书梁廷栋,以‘擅开战端、私通外夷’之罪,将袁崇焕革职下狱,关押于宁远大牢。喀喇沁部使者已被驱逐,关宁军群龙无首,后金已有反扑之势。”
“高第?梁廷栋?”朱由检咬牙切齿,眼中怒火如焚,“一个畏敌如虎、弃地百里的懦夫,一个满口仁义道德、实则嫉贤妒能的腐儒!他们竟敢动朕亲封的太子太保?!”
王承恩吓得跪地发抖:“陛下,这……这是文官集团反扑啊!他们见桐庐事败,便转而攻边将,意在动摇新政根基!”
“何止是反扑。”朱由检冷冷道,“这是要逼朕低头。他们知道袁崇焕是新政在军中的象征,杀了他,等于斩断朕伸向边疆的手。”他缓缓踱步,手指紧攥御案边缘,指节发白,“可他们忘了??朕不是靠他们才坐上这把椅子的。”
他猛然转身,喝令:“传旨:命锦衣卫北镇抚司即刻出发,持尚方剑直赴宁远,提审高第、梁廷栋党羽,凡参与构陷袁崇焕者,一律下诏狱!另,调宣府精骑三千,护送钦差前往,若有阻拦,格杀勿论!”
赵九渊凛然领命,正欲退下,朱由检却又唤住他:“等等。”
“陛下?”
“你亲自去。”朱由检盯着他,一字一句道,“带上朕的亲笔手谕。告诉袁崇焕??朕信他,胜过信这满朝文武。”
赵九渊重重点头,转身大步而去。
三日后,京师震动。
钦差抵达宁远当日,高第竟下令关闭城门,宣称“边地重镇,不得擅入朝廷鹰犬”。赵九渊未动怒,只命神机营炮队对准城楼,架起红夷大炮三门,炮口直指镇守府。
“再不开门,本官便替陛下拆了这座城。”
半个时辰后,城门吱呀开启。
高第跪迎于道旁,面如死灰。赵九渊当众宣读圣旨,将其当场锁拿,押解回京。与此同时,袁崇焕被释放出狱,将士百姓夹道相迎,哭声震天。有老兵跪地叩首:“袁帅不死,大明不亡!”
消息传回京城,百官哗然。内阁首辅李建泰病倒不起,礼部尚书称疾告假,东林党人心惶惶。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三日后,河南道御史周延儒竟上疏弹劾赵九渊“滥用皇权、僭越军制”,要求“还政于朝,肃清朝纲”。
朱由检看罢奏章,只是冷笑。
他召来王承恩,淡淡道:“把这份奏章抄一份,送到袁崇焕案头。再告诉周延儒??他的儿子,在扬州盐政贪墨八万两白银,证据确凿。”
王承恩一惊:“陛下,这……周御史乃清流名士,若公开其子罪行,恐激起士林公愤。”
“公愤?”朱由检仰天大笑,“他们骂朕暴虐,可他们自己呢?一边高谈‘君子不言利’,一边让子弟横行市井、霸占田产、勾结盐商!朕倒要看看,他们的‘清议’,能不能挡得住铁证如山!”
次日,刑部公开审理周延儒之子贪污案,人证物证俱全,百姓围观如潮。最终判斩监候,家产抄没。周延儒闻讯呕血三升,自行辞官归乡。
至此,朝中再无人敢公然挑战皇权。
然而,真正的风暴,仍在暗处酝酿。
一个月后,南京传来密报:徐霞客失踪了。
朱由检正在御花园巡视新设的“农政试验田”,听闻此讯,手中竹杖顿地,发出闷响。“徐霞客?那个游历天下、著《游记》的徐家子弟?”
“正是。”王承恩低声道,“据查,他三个月前离家,说是去西南考察水道,但沿途驿站皆无记录。锦衣卫追查至贵州黄平,发现他曾与一名蒙面僧人密会,之后便如人间蒸发。”
朱由检眯起眼睛:“蒙面僧人?可查到身份?”
“尚未查明,但……”王承恩犹豫片刻,“属下怀疑,此人极可能是影阁余孽。当年峨眉地宫破灭时,有一名主持秘仪的老僧逃脱,据骆思恭记载,那人精通‘心蛊之术’,能以言语惑人心智,令人甘愿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