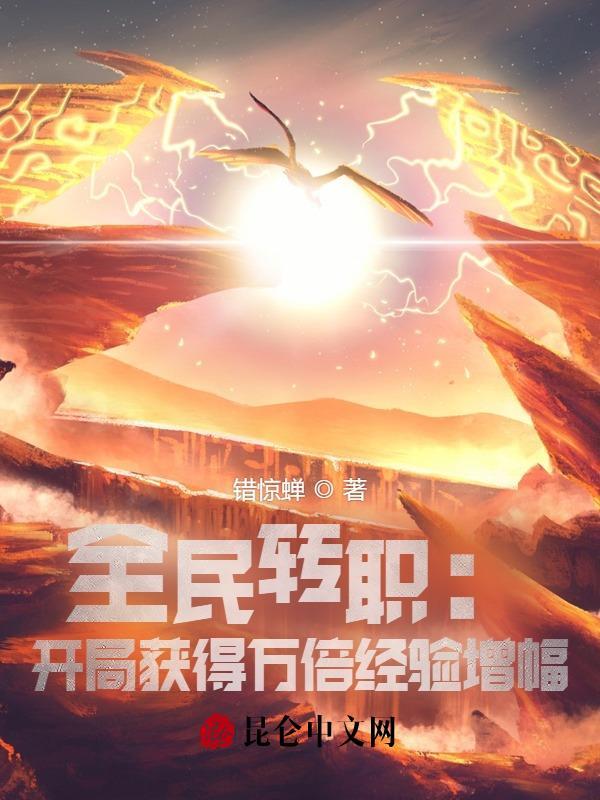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小白花?他装的! > 吃味(第2页)
吃味(第2页)
天边霞色烂漫,他白皙的脸在这片余晖中,越显媚色,眸子因为喝醉了,也搅动着细细情丝。
辞缘不接话,那台下的姑娘们越来越兴奋,各色各样的花儿,接二连三在他身后抛出流畅的弧度,他就那样靠在阑干前,深怕那些花儿砸不到他似的。
“不过来是吗?”她咬牙切齿。
辞缘微微歪头,鬓边绒花颤动,只差吸引狂蜂浪蝶。
卿如意忍无可忍,夺步上前,一把拽住他手腕,将他狠狠往身旁一带:“连师父的话都不听了吗!”
啪叽一下,一朵硕大的花苞正中红心,击中她太阳穴,不轻不重,却更让她火冒三丈。
那花苞落在地上,红艳艳的,好生张牙舞爪。
卿如意气得飞速回首,怒瞪了一眼闹成一锅粥的人群,姑娘们顿时收了笑,各个噤声,表情微妙地面面相觑。
辞缘却要弯腰捡那朵花儿,卿如意用力一扯他袖子,上去就是一脚,那花儿在脚下登时烂做一团。
她就那样踩着花儿,跟个炮仗一样守在辞缘身边,随时都会噼里啪啦炸开。
“师父,你生气了?”辞缘无措地看着她,任由她掐住自己,哪怕手腕传来一阵淡淡的疼。
卿如意哼了一声:“谁生气了?你要不拿面镜子照照,看看是有多放浪形骸!我就是看不惯你这样!”
辞缘若有所思看着她脚下,半天唔了声:“那师父踩花儿做什么?师父不是一向恪守道义,恩怨分明的吗?缘何要滥伤无辜?”
她脸腾地一下红了,狠狠剜了他眼,将花儿在脚下一碾,扯着他火急火燎离开望月台:“你别打岔!总之你就是不对!以后不准来这望月台,不准斜斜倚着,跟个浪子一样!”
辞缘温驯地由她牵着,看着她步履匆忙,好半天才低低道了声:“师父你是不是有点吃醋。”
卿如意脚步一顿,炸毛般回头:“谁吃醋了!你的事,为师还管不得了!”
那双凤眼噙着薄雾,乌泱泱的,直把她望,卿如意发热的头脑终于冷静些许。
耳畔恢复妓子们的歌唱声,丝竹琵琶,不绝于耳,再没有那些姑娘们的欢闹声了。
卿如意视线落于辞缘腕上,才发觉自己掐得分为用力,惹出淡淡红痕,她视线一跳,慌忙松开。
发热的头脑逐渐冷静——她到底在做些什么?她竟如此失态!
卿如意面色由红转白,深呼吸片刻,语气冷如寒冬腊月:“我是你师傅,教你如何做人,有什么问题吗?”
辞缘瞳孔一滞,腕上的疼痛忽然鲜明起来。
卿如意不再看他,大踏步向前走:“已经申时了,把游小世子叫上,还别个人情去。”
她突然转变的态度何其明显,可她还留有余红的耳朵尖,却全然出卖了她的本心。
辞缘目光追随她步伐,稳稳跟于她身后。
他不信,从他打破她底线那一刻起,她就给了他可乘之机,她方才那副模样,分明就是对他动了心,可她为何要装?为何要藏?
右手紧紧握拳,他睫羽扑簌。
家班众人也跟着卿如意,另分一间包厢。一时红香楼内,热闹非凡,一迭端盘之人鱼贯而入。
“酒上太多了,这位公子喝不得酒。”游逢安将那几坛酒减去大半,卿如意皱眉,原身喝酒不在行吗?不过她在现世里还没喝过酒,不知道自己酒量究竟如何呢。
话说这老鸨可谓是用尽了心思,不光给了最上等的雅间,就连唱功一等一的伶人,都送了进来。
雅间内烛光灿烂,照得人身上亮堂堂的,这可就看见了一张熟面孔,卿如意停下手中筷箸,不由多看了那人一眼。
游逢安关切道:“卿妹妹,怎么不夹菜?”
说完,便要夹那道红烧狮子头。
近乎同时,飞来一双筷箸,夹走盘中个头最大的狮子头,游逢安顺着筷箸方向一看,好巧不巧,又是辞缘。
二人目光相撞,擦出烈烈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