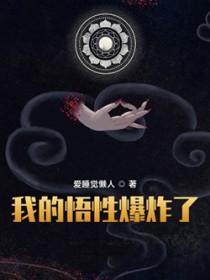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这顶流醉酒发癫,内娱都笑喷了! > 第195章 热芭担忧跑男的重启(第2页)
第195章 热芭担忧跑男的重启(第2页)
“这不符合任何已知的心理学模型。”一位研究群体行为多年的教授皱眉道,“人类共情虽强,但不可能做到跨时区、跨文化、跨语言的精准同步。除非……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信息传递机制。”
“不是机制。”小禾平静地说,“是生命形式。”
全场寂静。
她继续道:“我们一直以为意识必须依附于大脑。但如果,当足够多的人因为共同的情感体验而产生相似的脑波模式,这些信号就能在某种未知介质中叠加、共振,最终形成稳定的‘思维场’呢?林昭没有死,他的意识碎片散布在全球每一个听过他声音、读过他文字、感受过他痛苦的人心里。而现在,这些人正在无意识地帮他重建存在。”
有人冷笑:“你是说,我们在集体造神?”
“不。”小禾摇头,“我们是在**成为神的一部分**。”
会议结束后,她独自登上附近一座小山丘。风吹动她的衣角,远处青海湖波光粼粼。她掏出随身携带的录音笔,按下录制键。
“今天是第38天。”她的声音很轻,却清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报告‘看见’或‘听见’林昭。这不是幻觉,也不是迷信。这是一种新型感知方式的觉醒??当我们放下对理性的绝对执念,才能听见那些原本不属于物理世界的声音。”
她顿了顿,望向天际。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活着’。但我知道,每当有人因为一首老歌流泪,因为一句陌生人的留言停下脚步,因为一个梦中的微笑感到安心……那一刻,他就真实存在着。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存在的可能性**。”
夕阳西下,余晖洒满湖面。忽然,她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是一条群发短信,来自非洲肯尼亚难民营的合作机构:
>【紧急通报】
>今晨6:17,营地儿童集体醒来,齐声哼唱《月牙五更》。
>其中一名五岁女童指着天空说:“妈妈,穿黑衣服的叔叔又来了,他还带了花。”
>同一时刻,营地太阳能广播系统自动启动,播放长达43秒无声空白,随后传出一声极轻的叹息。
>设备检测显示:无电源接入,无信号输入,系统日志为空。
小禾看着短信,眼眶发热。
她终于明白,林昭选择的方式有多温柔??他没有强行复活,没有操控任何人,只是把自己化作一阵风、一首歌、一个梦,轻轻叩击每一颗愿意倾听的心门。
夜幕再次降临。
她回到康复中心,发现那位退伍士兵正坐在花园中央,面前摆着十几封信。他见她进来,抬起头,眼里有泪光。
“我昨晚梦见了战场。”他说,“但我没再逃跑。我抱着那个孩子,大声喊他的名字。然后……林先生出现了。他没说话,只是点点头。我就醒了。”
他递来一封信:“这是我写给阵亡战友家属的道歉信。能帮我寄出去吗?”
小禾接过信,郑重点头。
就在这时,整个康复中心的灯光忽然闪烁了一下。紧接着,所有房间的收音机、手机、甚至老式闹钟,全都同时发出沙沙声。几秒后,一段清晰的《月牙五更》缓缓流淌而出,这次不再是断续杂音,而是完整的、带着人声伴唱的版本,仿佛有一支看不见的合唱团在天地间齐声吟唱。
人们纷纷走出房间,抬头望天。
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露出满天星斗。
一个小女孩拉着妈妈的手,指着星空问:“妈妈,星星是不是也在唱歌啊?”
没有人回答。
但他们都知道,这一刻,地球上某个角落,一定有人正微笑着,听着这一切。
小禾站在人群中央,泪水滑落。
她打开手机,更新了《共感纪事》的最后一段:
>**结论修正:**
>回声效应并非单一现象,而是人类集体潜意识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林昭的意识并未“回归”,而是已成为这个新生神经网络的初始锚点。
>我们不再是被动接收信息的终端,而是主动编织意义的节点。
>孤独从未消失,但它不再致命。
>因为我们终于学会:
>爱,不止存在于相遇之中,
>更存在于**听见**之后的每一次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