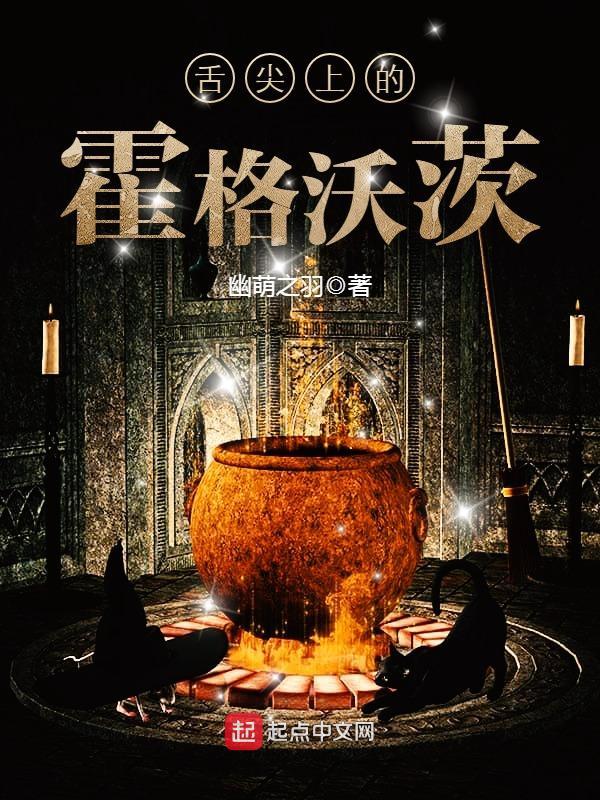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重生之剑影长佩 > 第29章 往事浮沉(第1页)
第29章 往事浮沉(第1页)
大约是睡觉之前想起了姜落云,雁惊寒久违地梦到了从前之事。梦里的时间混乱无序,他倏忽一夜从幼儿长成少童,温婉敬爱的母亲也变成了歇斯底里的疯妇。
雁惊寒本以为自己早已忘记那一日。但是如今往事如烟雾般涌来,不容退避地将他淹没其中。他才恍然惊觉,原来他从未忘记,竟连在梦里也记得如此清晰。
彼时的他尚且年幼,还未满八岁,正是闲不住的年纪。雁惊寒记得那日天气正好。自己如往常一般好不容易耐着性子练了功、完成先生布置的功课,便称人不注意偷偷溜去后山玩闹,及至到了晚间捕了两只兔子,这才心满意足地回来。沾了一身草屑泥土,还不忘去逗一逗自己才满三岁的弟弟,折腾得婢女小厮们一阵焦头烂额,在后面追了一路,好不热闹。
雁惊寒正拎着兔子在院子里和仆人们斗智斗勇,突听大门方向传来“砰”的一声。众人被这声响惊得愣了愣,不禁面面相觑。还是雁惊寒最先反应过来,径直往门口跑去。
接着他便看到了另他费解的一幕:他的母亲正昏迷不醒地躺在父亲怀中,发髻散乱,而他的父亲则一脸冷肃。
雁惊寒注意到对方手上还有一道伤口,虽然已经包扎好了,却仍有血迹渗出。他莫名有些心慌,眼看着雁不归面色不愉,瞥了他一眼便径直朝里走去,竟有些不敢开口。院中众人一时间更是跪了一地,噤若寒蝉。
雁惊寒到底年纪尚小,加之雁不归对他虽算疼爱但也一惯严厉,此时也只能跟在身后,眼睛一个劲往娘亲身上看。等到雁不归将姜落云放下了,看清对方惨白憔悴、尤带泪痕的面容,他终于忍不住扑过去趴在床边焦急问道:“爹,娘她怎么了?”
此时的雁惊寒还未意识到事情的本质,只以为是有歹人竟敢图谋不轨,伤了雁不归与姜落云。但他对雁不归向来颇为敬重,虽然心中奇怪是何人可以伤到他的楼主父亲,但也并不害怕。直觉那人定然早已经被拿下了,只是到底担忧母亲状况。
然而,雁不归听了他的问话,却不发一言,将姜落云放下就走。只留下冷冰冰的一句:“夫人身体有损,需安心静养,即日起便不要让她出门了。”
到了此时,雁惊寒方才察觉不对。他看了看守在母亲身边的秋菱,见她闻言猛然抬头看向雁不归,面带哀泣,张了张口却只是垂头不语。终于一转身追上去拉住雁不归衣袖,忙不跌问道:“爹,你不等娘亲醒来吗?”
雁不归步伐一顿,目光扫过他周身,面容越发冷厉。皱眉叱道:“成日里只顾玩闹,你的功法何时能有长进?”
说着一甩袖便朝院门走去,看到那两只兔子,又朝仆人吩咐道,“将这两只畜生处理了,好好督促公子练功。”
“是。”众人被他一身气势骇得不敢抬头。雁惊寒还未及阻止,已经有人上前将那两只兔子拎走。
但他此时也顾不得这个了,小小的雁惊寒心中突然涌起一种直觉般的惶恐,忍不住大声请求道:“父亲,父亲能否陪陪母亲,我。。。。。。我保证日后一定用心练功,不教父亲失望。”
他从来只在较为严肃正经的场合里称呼雁不归父亲,大都时候都如普通人家一般亲昵地喊他“爹”。但他话音刚落,雁不归却早已走远了,连头都不曾回一下。
雁惊寒自懂事起便知他的父亲乃是揽月楼高高在上的楼主,他威严持重、武功高强,旁人敬他畏他。但那只是旁人而已,他是雁不归的孩子,雁不归亦从来不吝于在他面前展示作为一个父亲的温情。他从来不知,他的父亲能对他和母亲如此冷漠。
秋菱去药堂请了人来替姜落云看过,大夫只说她只是急火攻心、情绪激动,并无大碍,过几个时辰即会转醒。雁惊寒放心不下不肯回房,就趴在床边眼巴巴守着。秋菱拗不过他,只得拿了被褥来替他披在身上,自己留心看顾着。
到了半夜时分,雁惊寒只觉耳边有人哀哀哭泣。他一个激灵睁开眼,便看到母亲已经醒过来了,正睁着眼睛抽噎流泪。秋菱默不作声,只在一旁替她擦泪抚背。
他连忙靠过去,焦急问道:“娘,你到底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
姜落云似乎这才发现他醒了。她静了静,睁着一双哭红的眼睛看了看他,突然嘶声大哭起来,这声音哀恸绝望。
雁惊寒看着她,见她在床上蜷成一团,仿佛自我折磨般抓挠自己的头发脸颊。他浑身一震,整个人吓坏了,只下意识扑过去制住她双手,不让娘亲伤害自己。
耳边听得姜落云悔极痛极的声音,一遍遍问道:“为什么?为什么?他答应我的。。。。。。一生不变、永世珍爱。为什么。。。。。。为什么?这才多久?不过十年?到底为什么?哈哈哈哈。。。。。。为什么。”这一声声“为什么”响在耳边,仿佛泣血的哀鸣。小小的雁惊寒拉着她的手,不禁也跟着落下泪来。
姜落云哭闹了近一个时辰,到了最后大约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