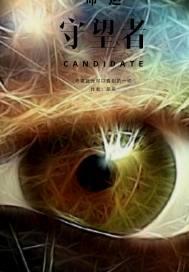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权臣成双 又生 > 3040(第29页)
3040(第29页)
朱昱修道:“谁让湖州官局这么干的?”
陆洗道:“郑国公姚澈。”
伴随着衣带之间金钩玉珩碰撞的脆响,又一人站出队列。
姚澈抢道:“陛下,湖州官局隶属于浙东织染局,此事乃浙东局调度无方所致。”
此言一出,满堂哗然。
朱昱修见许多官员用探寻的目光看着林佩,遂问道:“左相,浙东织染局如今谁人管事?”
林佩用平静的语气表明态度:“浙东织染使乃是林倜,鸿胪寺卿适才报过了。”
林倜咳嗽一声,把皇帝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陛下,臣就是林倜,臣并没有让下面的人囤积丝料,奈何江南官局半数以上由郑国公的本家掌控,他们阳奉阴违,臣力不从心啊。”
朱昱修听到这里只觉一团乱麻,已经捋不清其中的关系。
“陛下,然事情毕竟已经发生,臣不推卸责任。”林倜耐不住性子,补充道,“臣甘领惩罚。”
朱昱修道:“郑国公,林倜说的是真的吗?”
姚澈叹口气,颤颤巍巍地摇头道:“陛下,老臣上了年纪,平日在家只烧香敬佛,其余的实在是不知啊。”
陆洗道:“嘴上说不知,心里就真的不知吗?”
姚澈站在那儿,一副受尽了委屈的样子。
陆洗上前道:“陛下,臣要参郑国公蓄意囤积丝料、阻挠官私合营、庇护纵容亲属行凶杀人。”
朱昱修道:“有证据吗?”
陆洗斩钉截铁:“有。”
一个有字振聋发聩。
姚澈眯起眼,缓缓转过头。
钲响。
侍卫带人。
老妇在孙儿和儿媳的搀扶之下缓缓走来,每隔十步便跪地对天家行一次大礼。
另一边,犯人王良、薛超等被麻绳捆着,由柳挽押送到御前。
朱昱修欠身:“发生何事了?”
老妇人吓得面色苍白,不敢抬头:“草民……”
陆洗道:“阿姥,你有什么冤屈,都说出来吧。”
老妇人听到陆洗的声音,抓着救命的稻草,一五一十把事情原委说了出来。
——“回,回陛下,湖州官局贴出招工告示,因我家出价最低,所以拿到了两千匹花罗的单子,谁知交货之时,织作王良百般刁难,见我儿不肯屈服,竟雇凶取我儿性命。”
尧恩命刑部官员现场确认从案发地带来的卷宗和证物。
大理寺、都察院在旁监察。
刀具、衣鞋、赃物、名册摆到御前。
蜡泪沿着烛台落下,伴着殿中断断续续的抽噎。
除丁茂遇害一案,另有奸杀女工、虐待劳工致死、贪赃被告杀人灭口,都是铁证如山的命案。
姚澈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陆洗道:“王良,你记恨丁茂抢夺了本该由你支配的饷银,更不想从此以后被私营作坊分走官局的油水,所以雇江湖浪客杀人,恐吓民众,影响恶劣,十恶不赦,可还有什么辩解吗?”
王良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中透出疲倦,张了张口:“我认罪,只求给我一个痛快。”
陆洗道:“薛……”
“冤枉!”薛超拽着绳子往前爬,伸手去扯姚澈的绶带,哭喊道,“舅老爷救救侄儿,侄儿不想死啊!不都是你教我们这么做的吗?!”
姚澈一脚踢开:“放肆,我根本都没见过你。”
朱昱修道:“右相,你帮朕捋一下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