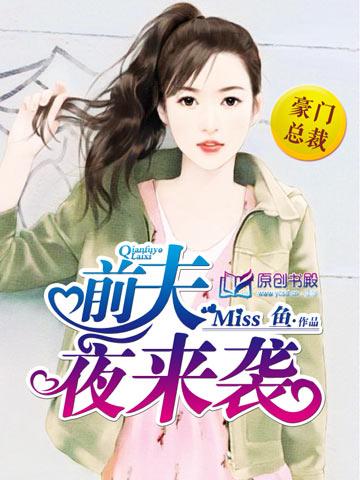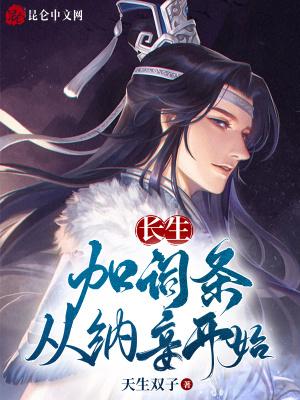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权臣成双 又生 > 7080(第32页)
7080(第32页)
二人走到正堂,分坐左右。
陆洗不知道林佩事先传唤了各部院,但他知道此时正好可以提出北伐。
“各位大人,关于鞑靼近期进犯鹞儿岭、凉州卫、广宁卫等事,陆某今早进宫请示了陛下,圣意尽在那阵磅礴有力的鼓声之中。”陆洗说道,“今夏,我领宣府十万主力北伐,以闻远为主将,董成为副将,北出独石,直取迤都。”
方时镜听说这个消息,一始没有说话,低头凝视帽冠系绳上的垂珠。
林佩道:“贺尚书,兵部调令、营训、镇戍以及兵器、马匹供应事项,请按右相的指令执行,涉及军制更改奏报中书省,其余一应可与平辽总督府谋定。”
贺之夏道:“下官明白。”
林佩道:“工部负责把粮饷从南方各仓运送到北京交给兵部武库司,夏至秋季完成一百五十万石粮。”
话到此处,董颢分明是顿了一下。
舍人捏紧笔杆,墨汁在砚台边沿凝成黑亮的圆点。
董颢道:“多少?”
林佩道:“一百五十万石。”
“今年勉强能做到,但估计明年就接续不上了。”董颢咬一咬牙,神色凝重,“前军攻下城池之后务必尽快在当地屯田,减轻国库的负担。”
这听起来是一句实事求是的话。
林佩道:“陆大人听见了?”
陆洗道:“听见了,我绝不贪功。”
林佩道:“董尚书,你也不要过于忧虑,过段时间我再与你商量整改漕运的事,现在你先全力支持前线的军需。”
董颢道:“好吧。”
林佩道:“礼部起草檄文,按制本月即应完成,考虑到方尚书要主持编撰大典事宜,几位大学士也各有分工,不如你们再推荐一名翰林来写,如何。”
方时镜抬起头,愁眉渐展。
他前些天才刚上过一道奏疏,规劝皇帝“偃武修文,止戈养民,以尧舜仁心垂拱天下”,既不赞成主动对鞑靼进兵,也就不愿意亲自起笔征讨檄文,好在是这下林佩没有为难。
“我和几位侍郎都商议了一下。”方时镜道,“翰林院确乎有一人可担此重任,这人姓祝名郁离,曾屡上《备虏疏》,力主‘以战止战’,言‘鞑靼跳梁,非大创之,终为九边患,宜选精锐出塞,犁庭扫穴,使胡马不敢南窥’。”
林佩道:“行,这个人我见过,湖州士子,面相斯文清秀,写文章却力透纸背。”
陆洗笑道:“你真是太周到了,没想到……”
林佩转过脸:“陆大人也早就认识祝郁离吧,毕竟他那般景仰你。”
陆洗连忙收住笑容:“认不认识无所谓,谁写都一样,合适就好。”
林佩道:“你刚才说没想到,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这次你只字不挑我的错处,还鼎力扶持。”陆洗起身行礼,“多谢。”
“不必言谢。”林佩抬手替他整理腰间玉带,动作自然,语气也很平静,“泱泱大国,万军统帅,出征就该有出征的样子。”
金线刺绣蟒纹在烛火下闪动。
牙牌、印绶、玉钩相碰,铿锵有声。
陆洗道:“知言,我出征去,你如何打算?”
林佩道:“我就在这里。”
陆洗道:“这里是哪里?”
林佩道:“抬头看看匾。”
陆洗仰起头,目光触到那四个字,会心一笑。
林佩道:“我在这里送你,也在这里迎你回来。”
经此过场,各部明确职责,上下齐心。
阜国朝廷做出了继迁都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决策——出师北伐。
*
七月初一,奉天殿前晨曦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