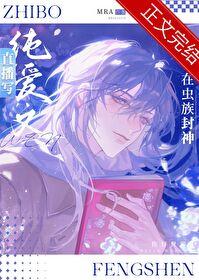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今天跟谁去 > 2玉米排骨汤(第1页)
2玉米排骨汤(第1页)
一年前
何喜推开旅行社的玻璃门,初春的阳光斜斜地洒在肩头。手机突然在上衣口袋里震动起来,隔着衣料传来细微的酥麻感。
作为喜帆旅行社三大股东之一,何喜近两年开始奉行“佛系接单”——能接到的电话就是该成的买卖,错过的便是无缘。不带团的时候,她的手机多半静音,到了夜里更是直接关机,这让另外两位股东张帆、方迁头痛不已。
上午带团,开的振动忘了调,要不搁她平时的习惯,怕是要到晚饭后才能发现这通电话,她从口袋掏出手机,屏幕上闪烁的“李萍”二字让她微微怔住,这可太新鲜了。
母女两人上一次通话是在除夕夜,更准确点应该是新年初一凌晨。
父亲去世后,每年除夕何喜都会给妈妈李萍打一个电话。除此之外,互不打扰。
同往年一样,何喜在除夕这天给李萍打了个电话,提示“正在通话中”,她裹着毛毯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地看完了一个小品加一个舞蹈节目,给李萍打了第二通电话,仍是“正在通话中。”
李萍回电时,何喜已经在沙发上蜷缩着睡着了。电视屏幕泛着冷清的蓝光,春晚重播正放到第一个小品,观众的笑声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何喜眯着眼看手机屏幕——凌晨两点十七分。她接通电话的瞬间,那头骤然炸开的欢闹声像潮水般涌来:孩童雀跃的尖叫,此起彼伏的烟花爆破声,还有觥筹交错的清脆碰杯声……何喜甚至能想象出他们一大家子此时生动鲜活的幸福模样。
通话内容枯燥无聊,何喜老老实实地祝福李萍一家人新年快乐,李萍道谢后,叮嘱她一人在外注意安全,又老生常谈地诉说自己身在吴家的难处,试图解释为何不邀她来过年。
挂断时,何喜看了眼通话时长,一分五十秒。
何喜偶尔会冒出些“大逆不道”的念头——比如这每年一度的通话,与其说是母女问候,倒不如说是某种心照不宣的生存确认。
电话那头传来的每一声“喂”,都在无声地询问:你还活着吗?而这边回应的“嗯”,则是同样克制的回答:托您的福,还没死呢!
对于这通“计划外”的电话,何喜心情复杂,有担忧、有喜悦,不过最终好奇占了大头,她真的想不出,得是多么大的事,李萍才会主动给她打电话,她接听:“妈妈。”
李萍急急开口:“何喜啊?你是不是没有男朋友?”
哦,原来是为这样一件不起眼的小事。
何喜慢悠悠地往公交站走,平静地说:“没有。”
李萍的声音洋溢着喜悦:“那个,你吴叔叔的生意伙伴来咱们家,看到你的照片,说想和你认识一下,他条件很不错的,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何喜沉默,她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继父吴远辉今年都五十岁了,生意伙伴再年轻能年轻到多少?
她今年二十六,也在奔三的路上了,确实不能算是小姑娘了,可那也不代表她要配老男人吧?
再说了,她在西城工作,回海城一趟飞机倒高铁的,得折腾小半天。
何喜不说话,李萍也不在意,似乎是在翻日历,她听见纸张飞起的声音。
李萍在电话那端嘀咕,“最近的假期……马上就五一了,要不你五一回来吧?”
何喜无奈,开口打断:“妈,五一是旅游小高峰,我忙都忙不过来,哪有空回去?公交车到了,我先上车了,我没空,也不想见,他要是想认识我就让他来西城找我吧。”
何喜挂断电话,长舒了一口气,公交车并没有来,她抬头看路旁的玉兰花,四月初正值玉兰盛放之时,一树白花开得恣意。
海城也有玉兰花,不过因为地处东北,天气寒冷,不像西城这样随处可见。
何喜记得,当年她读杂书,看见书上说玉兰的花苞毛茸茸的,花朵直挺挺的朝上开,觉得这花有意思,想一探真容,和石磊找了好久,最后得知只有海城大学有,他们俩狗狗祟祟的跟着人流躲避门卫进校园,才得以一见。
当年费劲心力才能看见的如今唾手可得。
其实,也就那样。
公交车停下,何喜收回视线,刷卡上车,没有空座,她抓着扶手,想象自己是一只随海浪漂浮的小船,随着公交车前后摆动。
五站之后,她下车,公交站后身是个露天的小型菜市场,也是何喜回家的必经之路,她慢吞吞地走着,出了市场手上便拎了排骨和玉米。
再往西走,穿过一个长长的巷子,便是她住的小区南门,这小区有年头了,也没门禁,小铁门就大咧咧地敞开着,小区里头一半是当地的老年人,另一半则是附近大学的学生。
何喜推开单元门,爬到六楼,翻出钥匙开门,屋子是两室一厅,七十平,对她一个人来说甚至有点大了。
她换了鞋,系上围裙,排骨焯水,葱姜炝锅,排骨煎至两面金黄,加水咕嘟咕嘟炖出肉香,加糖提鲜,再把玉米丢进去,坐在客厅刷了会儿手机,关火盛菜。
独居的苦恼就是永远有剩饭,这锅玉米排骨汤她只喝了一半,就吃不动了,只好放进冰箱,作为明天的午饭。
洗了澡,见时间尚早,便拿起琵琶弹了会儿,天渐渐暗下,何喜收了琵琶,拿出乐高继续拼烘焙屋。
那次通话后,妈妈又打过好几次,时间掐的精妙,她前脚刚叫游客们自由活动,后脚电话就响了。
有那么几个瞬间,何喜险些产生了李萍很爱很爱她的错觉。
如果不爱她,怎么会把她的休息时间记得这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