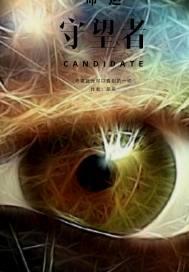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被恶龙抢走之后全文免费阅读 > 4050(第22页)
4050(第22页)
伯宜斯依旧没有任何该有的生理反应。
他没有抗拒,也没有迎合,就像一尊没有温度的精致雕像。
厄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他喘息着抬起头,不敢置信地看着伯宜斯毫无情动迹象、甚至带着嘲讽的脸。
“为什么……”厄的声音因为欲望和不解而沙哑。
伯宜斯冷淡地看着他,却是勾出了一个残酷至极的笑:
“因为我对你,起不来啊。”
“现在,带着你的花,滚出去。”
厄脸上的血色和热情瞬间褪得干干净净,眼睛里迅速积聚起水汽,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
他哭了,哭得像个被彻底抛弃的孩子,委屈又绝望。
伯宜斯硬起心肠,闭上眼睛,不再去看那张梨花带雨的脸。
他怕自己再多看一眼,又会犯贱地心软,会忘记心口那道从未愈合的伤疤,会忍不住像过去无数次那样,伸手替他擦去眼泪。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哥哥……”厄哽咽着,徒劳地试图解释,一边哭一边慌乱地找着借口,“你肯定是太累了……对,是这里不舒服,我们……”
伯宜斯无动于衷。
突然间,厄抬起手,房间内所有的灯光瞬间熄灭,陷入一片彻底的黑暗。
他摸索着,用力抱住伯宜斯,将脸埋在他的颈窝,声音闷闷的,带着哭腔说道:“哥哥睡觉吧……我们睡觉……”
伯宜斯简直无语。外面明明有一张奢华的大床,这人偏要和他挤在笼子的地毯上。
真有病。
厄紧紧地抱着他,不敢再提刚才的事情,也不敢再有任何逾矩的动作。安静了很久,他才小声地开口:“那个侍女,我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因为哥哥拒绝了她,哥哥是想留在这里的,对不对?”
伯宜斯知道今晚是赶不走他了,也懒得再浪费口舌,冷声道:“闭嘴。”
厄立刻噤声,乖巧得不可思议。
一片死寂的黑暗里,只有两人清浅不一的呼吸声。
那束被伯宜斯随手放在一旁的白色洋桔梗,在黑暗中散发着淡淡的荧光。
伯宜斯睁着眼,望着那片模糊的白色光晕。
洋桔梗,还有另一种花语。
无望的爱。
后来的几天,厄每晚上都会准时出现。
他每天都穿着仿照过去制定的衣服,梳着少年时期的发型,偏执地扮演着清澈温柔的“厄”。
学着少年时笨拙地亲吻和拥抱……他变着花样地“讨好”伯宜斯。
可这一切,换来的只是伯宜斯更深沉的冷漠和无声的抗拒。那双曾经会为他亮起、会为他担忧、会为他盛满温柔笑意的眼睛,如今只剩下冻彻骨髓的寒意和……厌倦。
是的,厌倦。厄清晰地读懂了那种情绪。
伯宜斯甚至懒得再对他生气,懒得理会他的疯狂。就像看着一场与己无关,拙劣又无趣的表演。
厄宁愿伯宜斯打他骂他,至少那证明伯宜斯还在意他,情绪还会因他而波动。
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勉强,眼神里的光亮逐渐被阴霾取代。终于,在某一天晚上,他所有的伪装的温柔和耐心消耗殆尽。
他的表情彻底冷了下来,一言不发地站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金笼。
伯宜斯看着他消失在门外的背影,嗤笑一声。
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听见脚步声去而复返。
厄再次走了进来。
他的手里,拿着一个精致小巧的水晶瓶,里面晃动着泛着微光的紫色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