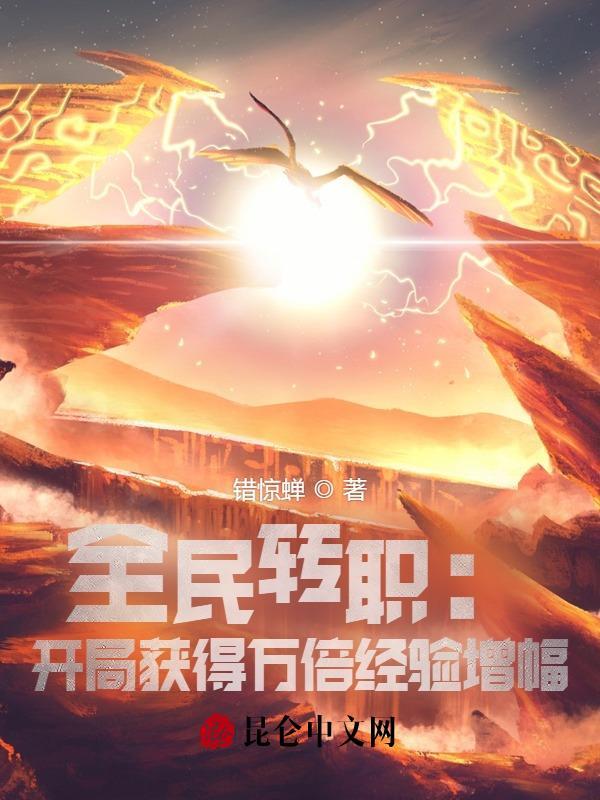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开封101路公交线路图 > 第十四章 徐评的尸体(第1页)
第十四章 徐评的尸体(第1页)
冬至过后,天冷得紧了。家家户户开始储存冬菜,以备冬季里使用。
每日天不亮,运送蔬菜的马车就挤满了道路,姜豉、红丝、末脏、鹅梨、榅桲、蛤蜊、螃蟹等,源源不断被送入京城。
州桥往南到龙津桥,这一条街上都是卖“杂嚼”的,水饭、熬肉、干脯等常年都有,冬日里的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须脑子肉最受欢迎。
龙津桥边的一个摊子上,几个跑腿的闲汉正聚在一处吃油?。
这是一种油炸的蒸饼,里面裹了豆馅,过水之后油炸,三浸三炸,又酥又脆,口感有点像今天的生汆丸子,只不过更香些,跑累了的闲汉吃上三两个,又香又扛饿。
一个闲汉一边咬着油?,一边说道,“听说,杭州一大户商家,因着与市舶司分赃不均,竟是闹到汴京来了,两边厮闹得甚是厉害。那市舶司也真的是,有钱大家一起分,怎能好处都叫他一人占了去,他吃肉,竟不许人喝汤,难怪人家不依。就好像这油?,若是能给一碗蜂蜜,我必不会独自享用,定要拿出来与人分的。”
旁边一个人笑他道,“瞧你这点子出息,一碗蜂蜜你就降了?若是我家有这么大的生意,莫说是亏了一些,即便是要分出五成的利,我也得让。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娃儿套不到狼,你不让些利,人家怎会有生意给你做?若我说,不如两下里约到那遇仙楼正店去喝上一顿,依旧照常赚着钱,总比这打打闹闹的强。”
第一个闲汉便道,“嗐,定是谈不拢,这才闹了起来。”说着,又一脸神秘的样子笑道,“听说,有的商家为了拉拢官员,竟是送礼都送到府宅内院去了,说不得,大娘子小娘子都要照顾到,这少不得又是一笔开销。唉,只是可怜咱们这样的人,每天只能跑腿赚个辛苦钱,不像人家,坐在家里动动嘴皮子,银钱就送上门来了。”
对面一个桌上,一人正在吃鹌鹑馉饳儿,一手还拿着一个?拍吃着,听了两个闲汉的话,他吃吃地笑了出来,抹了抹嘴,指着他二人笑道,“哪里如你们说的那般简单,这市舶司管着一方口岸的进出贸易,有多少货,多少条船要经他们的手。那商户本就富甲一方,又与市舶司盘恒已久,其中的勾连牵绊哪里是我们能想得到的。依我说,这是积怨许久,不知压了多少年,如今才一并发作了起来。且看吧,此事定有别的缘故在里头。”
那几个闲汉听了,便笑这人说话更不着边际,又吃着油?,一边说笑厮闹去了。
旁边一老者絮絮说道,“官商争利由来已久,今日你觉赚得少,明日他嫌吃了亏,说来说去,不过都是别人碗中的鱼肉,还有那更贪心的,只不过我们瞧不见罢了。”
老人的声音虽低,说的话却是一针见血,只是闲汉们却不以为意,又哄笑了一阵,吃完了油?,便各自散了。
相邻不远处,一年轻男子独自坐在矮桌前,他刚吃了一碗野菜馉饳儿并两只笋肉炊饼,一面听着众人的议论,一面喝光了碗里的汤。他站起来会了账,独自向过州桥方向走去。
御街一直南去便是过州桥,这里民宅较多,街上行人渐渐多了起来,经营各色吃食的摊主们奋力吆喝着,招揽生意。
展昭绕过行人摊贩,径直向漕运司徐评的府宅方向走去。
白玉堂散出去的邸报,加上他让王延喜在瓦舍里讲的话本子,已经开始流传开来。这种官商勾结的轶闻趣事,最适合在街头巷尾传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谈资。
没过两日,便被添油加醋,变成几个不同的版本流传着。
若是往常,这些流传的趣事,便如话本上的故事,一笑便罢。
但年下三司和转运使司接连出事,加上市舶司的官司,有些人心中惶恐不安,更听不得一点扑风捉影的话,竟是风声鹤唳起来。
如此一来,白玉堂敲山震虎的目的达到了,他知道此时老虎定是寝食难安,过不了多久便会有所行动,自己若想要引虎下山,便要再加一把火,将山敲得再响一些。
一大清早,白玉堂换了身衣裳,拿茶水漱了口,揣了一包紫苏梅子在怀里,出门向徐评家方向走去。
才走不远,便见展昭匆匆赶过来。
展昭迎面瞅见白玉堂,还未开口,只听他问道,“这么早,展缉司是要往哪里去?又要到谁家府中去串门子么?”
展昭听了这话,不免瞪了一眼,引他到路边,压低声音问道,“今早死了一个管漕运的官员,街上人说,他家大娘子便是个放印子钱的,还在外面偷偷养了个汉子,与你昨天说书的故事一般无二。我问你,这人的死,和你有没有关系?”
白玉堂听了展昭的问话,上下打量他一番道,“缉司好聪明,竟猜到了那话本里的乌家便是暗指我白家。但我家可不曾偷奸,至于这死的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