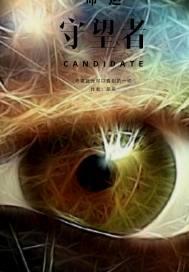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迫嫁豪门免费阅读 > 5060(第15页)
5060(第15页)
这种巨大的、足以撕裂灵魂的羞耻和绝望,远比刀锋更锋利。
他宁可用最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也绝不愿在亲人面前承认这不堪的身份,承受那怜悯或震惊的目光。
死,对难得清新起来的他而言,反而是解脱,是保全最后一点摇摇欲坠的尊严的方式。
沈照山无声地叹了口气,指尖无意识地划过冰冷的窗棂。
恰好就叫崔韫枝撞上了。
也不知道那个“疯症”的由头,她信吗?
就在这时,内室禾生那压抑的啜泣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带着巨大惊喜和难以置信的轻呼。
“殿下?您醒了!您终于醒了!”
沈照山猛地回神,目光骤然转向那紧闭的房门,方才所有的沉思和冷峻瞬间被另一种更为迫切的情绪取代。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大步流星地推门而入。
*
崔韫枝眼睫颤动,费力地掀开沉重的眼皮。
略微刺目的光线让她不适地眯了眯眼,意识如同沉船般缓慢浮出混沌的水面。
喉咙干涩得发疼,身体像是被拆散了又重新拼凑起来,绵软无力。她第一反应是抓住离自己最近的人、也便是禾生的胳膊,声音嘶哑微弱,带着急切的恐慌:“王……王隽呢?他……他说了什么?”
帷幔外,那道刚欲掀帘而入的挺拔身影骤然僵住。
沈照山的手停在半空,指尖距离薄如蝉翼的鲛绡帷幔仅寸许。
那句带着病弱气息却清晰无比的“王隽”,像一根冰冷的针,精准地刺入他杂乱的思绪。
崔韫枝问完,混沌的脑海才猛地闪过昏迷前那一瞥。
不对……不对,是沈照山吗?
近日来连日的入梦,让她有点儿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她转向禾生,刚想开口问问,话音未落,帷幔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猛地掀开!
沈照山高大的身影立在床前,逆着光,面容隐在阴影里,只有那双幽蓝的眼眸亮得惊人。
他周身裹挟着尚未散尽的寒意和一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
禾生被他周身散发的冷冽气势吓得一哆嗦,下意识想护在崔韫枝身前。
“出去。”沈照山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目光甚至没有从崔韫枝苍白的脸上移开。
禾生担忧地看了一眼自家殿下,在沈照山无形的威压下,只得惶恐不安地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内室只剩下他们两人,空气凝滞得如同灌了铅。
沈照山一步步走近床榻,靴子踩
在光洁的地砖上,发出清晰的声响,每一步都像是踏在崔韫枝紧绷的心弦上。
他看着床上那虚弱得仿佛一碰即碎的人儿,看着她因惊吓而微微睁大的眼睛,看着她唇上那抹被他闯入打断而未来得及擦拭的、已然有些斑驳的胭脂红。
那颜色刺得他眼睛发疼。
原本想询问她身体如何的话语,在舌尖滚了滚,出口时却淬满了控制不住的讥讽:“殿下对心上人,倒真是……从一而终。”
他的声音低沉缓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在崔韫枝心上。
崔韫枝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充满恶意的讽刺砸得懵了一瞬,心头的委屈和方才被王隽带来的巨大冲击瞬间翻涌上来。
“你……”她喉头哽住,又惊又怒,“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沈照山像是被她这无辜的反问彻底点燃了压抑的怒火。
他猛地俯身,带着一股凛冽的寒风逼近,一手撑在她枕边,另一只手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狠狠捏住了她的下巴,强迫她仰起脸直视自己。
他幽蓝的眼底翻涌着崔韫枝从未见过的、近乎失控的怒火,呼吸灼热地洒在她脸上。
“我什么意思?”他几乎是咬着牙,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诛心,“你和他关起门来,都说了些什么?”
“沈照山!”崔韫枝浑身剧震,脸色瞬间惨白如金纸,连唇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尽了。
那些被刻意遗忘的记忆,一点儿一点儿萦绕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