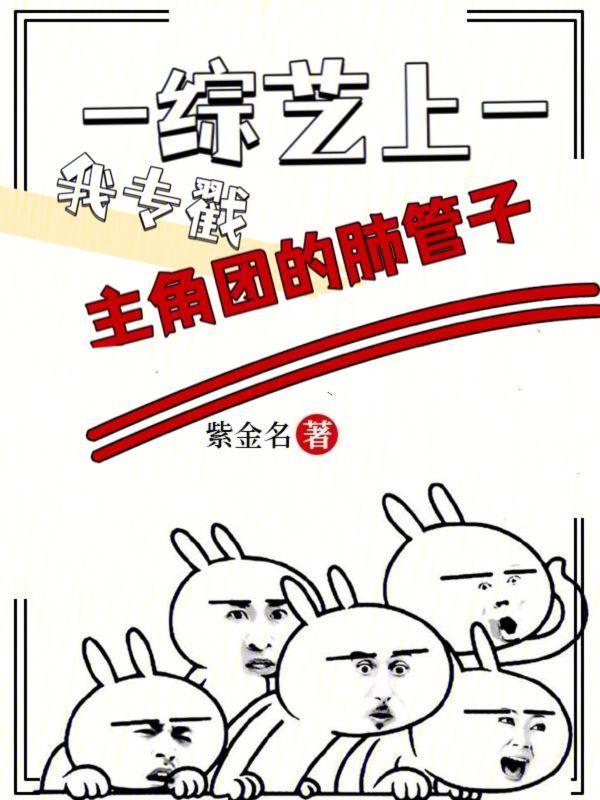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迫嫁豪门免费阅读 > 9095(第7页)
9095(第7页)
然而,这微笑瞬间凝固了。
鸦奴……沈照山……
她竟然又想起他了。在任何一点与过去相关的缝隙里,他的名字、他的身影都会无孔不入地钻进来,提醒着她那锥心刺骨的失去。
心口猛地一抽痛,手下意识地一重。
“嘶……”老人吃痛,缩了一下脖子。
崔韫枝立刻从回忆中惊醒,慌忙松开手,连声道歉:“对不起,爹,弄疼您了……我轻点,我轻点……”她放慢了动作。
崔韫枝就那样跪坐在那里,一点点,一梳梳,极有耐心地梳理着父亲杂乱的白发,仿佛要将这些年错过的时光、经历的苦难,都在这轻柔的梳理中抚平。
不知过了多久,久到窗外的天色都有些暗了。
一直安静任她梳理的老人,忽然缓缓地、极其缓慢地转过了头。
他用那双因为长久的监禁、折磨和疯癫而浑浊不堪的眼睛,定定地看向崔韫枝。
奇异的是,那一片混沌之中,此刻竟仿佛透出了一丝极其微弱的、属于过往的清明。
他伸出枯瘦如柴、布满老茧和伤痕的手,没有碰自己的头发,而是颤抖着,轻轻地、极其温柔地落在了崔韫枝的头顶。
老人张开手臂,将那把瘦弱却依旧残留着一丝熟悉气息的怀抱,向着她敞开,将怔住的她轻轻揽入怀中。
他的手笨拙地、一下下地拍着崔韫枝的背,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哄着那个因为摔倒而哭泣的小女孩一样。
“别怕……柔贞……别怕……爹在……”
这一下,崔韫枝一直强撑着的、摇摇欲坠的堤坝,轰然倒塌。
她再也忍不住,猛地扑进父亲那瘦弱却温暖的怀抱里,伸出手紧紧环住他嶙峋的腰背,将脸埋在他带着药味和陈旧气息的衣襟里,嚎啕大哭起来。
像一个在外面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可以放肆哭泣的港湾。
老人似乎并不完全明白她为何哭得如此伤心,他甚至可能已经不记得自己是谁,不记得怀中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经历了怎样的事情。但他只是本能地抱着她,轻轻拍着她,重复着那句最简单的话:
“别怕……别怕……”
崔韫枝窝在父亲的怀里,忽然好恨、好恨。
*
别院里的日子始终被一种刻意维持的平静包裹着。崔韫枝将她父亲妥帖安置,看着庭院中那跑来跑去的身影,始终不知道该说什么。
前朝废帝,还能或者已经算是上天开恩。
崔韫枝不知道……不知道沈照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盘算着救出老皇帝这件事的,但就军队驻扎的时间来看,不会是一时起意。
但崔韫枝不想再想了。
老人像个懵懂的幼童,除了偶尔能清晰地唤出“柔贞”这个名字外,对世间万物都失去了认知,过往的尊贵或是苦难,皆化为一片空白。
崔韫枝对此沉默以对,不追问,不探究,只是日复一日地悉心照料。
她让沈驰羽陪着外祖父在院子里玩耍。一老一少,坐在秋日暖阳下的石阶上,用枯黄的草叶笨拙地编着蛐蛐,往往就能安静地消磨整个下午。
而崔韫枝自己,则像一尊被抽走了灵魂的精美木偶。她大多时候只是沉默地坐在厅堂的主位上,眼神空洞地望着门外庭院里渐次凋零的草木,对周遭的一切都缺乏反应。
在一个秋高气爽、阳光却带着凉意的午后,赵昱再次前来复命。
禾生如临大敌,她几乎是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崔韫枝,拼命摇头,试图阻止这次会见。
她太了解自家殿下了,这种死寂的平静比歇斯底里更可怕,内里早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这让她想起多年前,殿下生下小殿下后不久,也是这般万念俱灰的模样,最终选择了决绝地跳下悬崖。
然而崔韫枝只是极其缓慢地摇了摇头。
“让他进来。”
赵昱快步走入厅堂,他一身风尘仆仆,脸上带着连日奔波未得休息的深刻疲惫,战甲上甚至还能看到未及清理的尘土与暗色痕迹。他不敢直视主位上的崔韫枝,进门后便单膝跪地,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头颅低垂。
厅内陷入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
崔韫枝垂眸看着跪在下方的赵昱,没有任何情绪,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压力。时间一点点流逝,只有秋风穿过堂前,卷起几片落叶发出的细微沙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