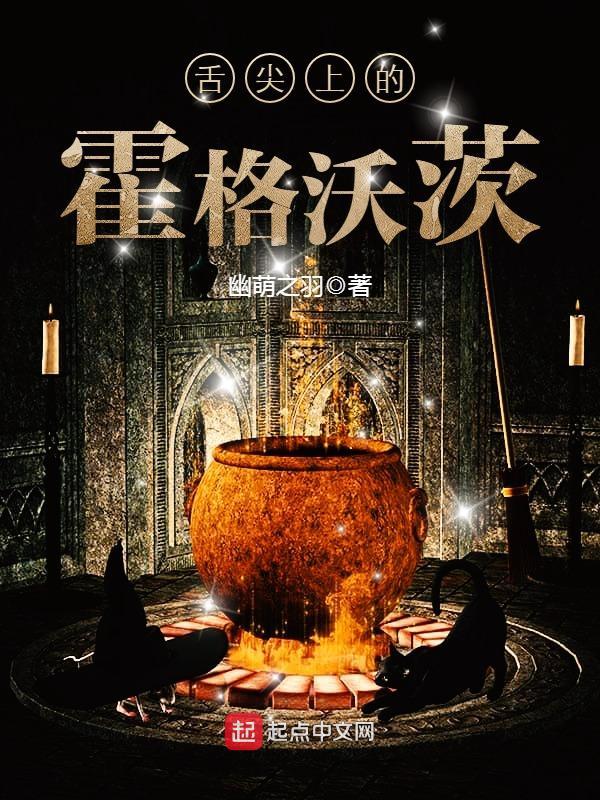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穿书后我跟死对头在一起了 > 太子殿下好像狗啊(第2页)
太子殿下好像狗啊(第2页)
可当着太子这封建专治头头和谢辞这头头鹰犬的面讲德先生赛先生,讲民主科学,岂不如同摸老虎屁股?
她偷眼瞥向萧彻,见他歪着头,眼神发直,估计是听不懂。
还好他是个傻子。苏意晚心想。
再看谢辞,眉头微蹙,却非怒色。
定然是隐忍不发,等着回宫向皇上打小报告,这个黑心的!
白若蘅继续道:“诸位可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知‘苛政猛于虎’?这‘德先生’,便是说君与民、官与民,原该是平等相待,而非一方压榨一方。昔日商纣造鹿台、剖比干,视民命如草芥,终落得自焚而亡;周武王吊民伐罪,与百姓同甘共苦,方有周朝八百年基业。如今苏州水旱连年,官府却只知加税,农户们种一亩桑,要缴三分之一的税,种一亩粮,还要再缴二分之一,逼得人卖儿鬻女,这便是失了‘德先生’的道理!”
堂下有学子忽然抬眸,声音清越如竹:“白姑娘说得是!这样的官府,如何能让百姓信服?”
白若蘅点头,目光扫过堂下的学子:“正是此理。‘德先生’不是要大家反了朝廷,而是要让为官者明白,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了,国家才能稳。就像这启智堂的竹篱,若是根脚松了,再高的墙也挡不住风雨。”
苏意晚听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檐下铜铃“泠泠”响过,学子们收拾书卷的窸窣声渐远,她才悄悄松了口气,用汗湿的手轻轻拽了拽谢辞的广袖,意欲试探他的态度。
“你觉得白姑娘方才说的话怎么样?”
“白姑娘说的没错,‘苛政猛于虎’,虎兕食人还挑肥瘦,苛政却连骨头都不剩。”谢辞看向被苏意晚攥出褶皱的袖口,皱了皱眉,把袖子往外抽了抽。
苏意晚这才察觉俩人过于亲密了,赧然一笑,接着问:“你没有觉得……白姑娘言论过于激进和反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心,苏州本就像被强权压绷的弦,积怨难返,颤出些裂帛之声,再寻常不过。”毕竟这地方,在他前世也是出过像“独眼神将”那样的反贼枭雄,见怪不怪了。
况且白若蘅所言亦有可取之处,只是在言论上还需约束一番,这些他自会找沈砚之相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他不会不懂。
看来白姑娘的头颅暂时不会搬家。苏意晚舒了口气,思忖道:谢辞这厮还是讲几分道理的,没有那么阴险小气。
一道阴影罩了过来。
“我竟不知,老师与家姐关系这样好,凑得这样近,私语喁喁,旁人见了,姐姐的清誉还要不要?”
“休要胡言,姑娘家的名声金贵,我与你姐姐不过是论及白姑娘的讲学。你既在旁听着,可有高见?”
一丝茫然跃上萧彻面庞。
他当然听懂了那占他便宜女子话里的反意。
不过那是他老子该操心的事儿,不在他这个“傻太子”考量范围,在谢辞面前他只要装傻卖乖,不打草惊蛇就好了。
“是为师失职,白姑娘言谈深意,待回去后为师再同你讲解。”
三人闲谈被白若蘅打断。
“各位不妨尝尝我这儿的饭食?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胜在家常小意。”
她说这话时,目光停留在萧彻的面上。她其实是想给她的小远再做顿饭。
她只能寄一个母亲可怜的心意于这个和他的小远有七分相似的少年身上。
萧彻方想拒绝,但触到白若蘅眼底殷切期待,下意识把话咽在肚子里,和着苏谢两人一同点头应谢。
方走到院心的竹桌旁,就听见院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沈砚之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娘子!事情都办妥了!”
白若蘅眼都不抬,“大男人办事风风火火的,聒噪死了。”
“这位是?”萧彻问道。
“我的同窗旧友,白姑娘的夫婿,现任苏州同知。”谢辞解释道,随后附耳朝沈砚之喃语了几句。
沈砚之立马惶然向萧彻行礼,“下官沈砚之见过太……萧公子。”
白若蘅翻了个白眼,心想自家官人当官当傻了连囫囵话都说不明白,官里官气的。
见苏意晚亦无异色,似是相识,萧彻心里莫名醋意翻涌。
怎么苏意晚连谢辞的同窗旧友都见过了?下一步俩人是不是就要见双亲论婚期请圣上赐婚了?
奥对,苏意晚没有双亲,谢辞也是孤家寡人一个……
那他俩岂不是更狂浪放纵了!
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