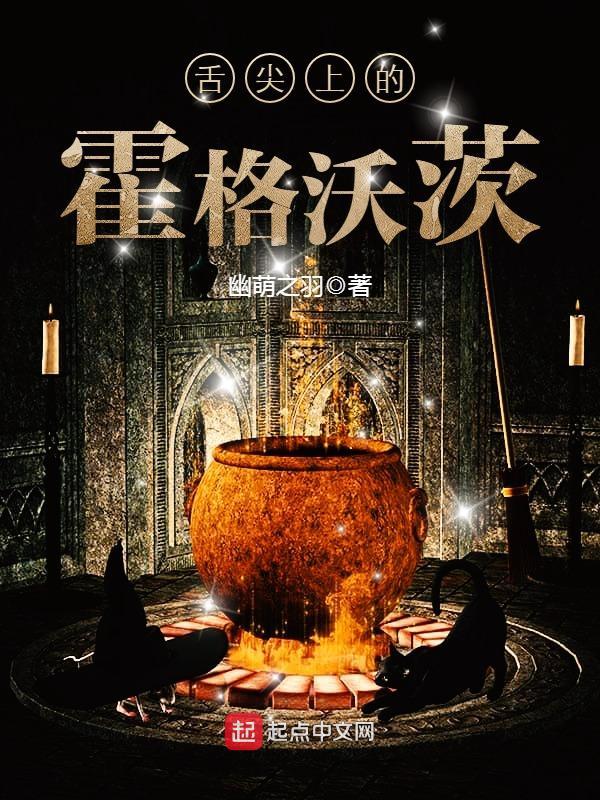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原来我才是表情包 > 我要考市一中(第2页)
我要考市一中(第2页)
一瞬间,失落、不甘、羡慕、仰望……无数复杂的情绪如同沸腾的岩浆,在阮绵绵心底猛烈地翻涌、冲撞!凭什么?凭什么他可以在那里?凭什么自己连重点班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那个名字,像一把钥匙,猛地打开了她心中某个被压抑的、名为“极度渴望”的阀门!一个声音在心底疯狂呐喊,盖过了所有的自怜和失落:我也要去那里!我也要去市一中!我要和他在同一个地方!我要证明,我不比任何人差!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便如同燎原之火,瞬间吞噬了所有的沮丧,只剩下一种近乎偏执的、燃烧着的决心!她的眼神骤然变了,不再是失落的空洞,而是燃起了一种灼人的、孤注一掷的光芒!
她猛地转过头,看向身边还在试图用“吃冰”安慰她的肖怀宇。
夕阳的金辉落入她清澈的眼底,那里面的火焰让肖怀宇心头莫名一跳。
阮绵绵的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坚定,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像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我要考市一中。”
肖怀宇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他像是听到了什么极其荒谬的笑话,眼睛微微睁大,带着毫不掩饰的错愕和……难以置信?
“你?考市一中?”他像是确认般重复了一遍,尾音上扬,充满了荒谬感。
随即他摇摇头,眼神里是赤裸裸的“你受刺激疯了吧”的意味,甚至带着点“别闹了”的安抚,“用你的芭蕾舞步跳过去吗?还是打算靠意念考进去?”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只是她受打击后一时冲动的气话,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快就会在冰冷的现实面前破灭。他甚至觉得有点好笑,刚才那点沉重的气氛都被她这“孩子气”的宣言冲淡了。
他嘴角重新勾起那抹熟悉的、带着点痞气的、看热闹似的笑容,等着她像往常一样被他打击后气鼓鼓地反驳或者放弃。
然而,阮绵绵迎着他毫不留情的目光和戏谑的笑容,眼神没有丝毫动摇,反而更加锐利和坚定!那燃烧的决心非但没有被他的冷水浇灭,反而像是淬了火,更加凝实,更加灼热!
“对,”她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却蕴含着破釜沉舟的力量,一字一句,清晰地砸在两人之间的空气里,“就是芭蕾。我要走芭蕾特招。市一中有艺术特长生名额。文化课分数线,我会拼了命去够!”
“芭蕾特招?!”肖怀宇脸上的笑容和戏谑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被巨大的震惊和难以置信取代。
他像是第一次真正认识眼前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孩,上下打量着她,仿佛想从她纤细的身体里找出那份疯狂的来源。
“你……你认真的?!”
他的声音拔高了,带着一种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急切和焦躁,“特招名额才几个?全市多少学芭蕾的盯着?竞争比裸分还惨烈!而且……”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她纤细的脚踝,眉头紧紧锁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你确定以后要走芭蕾舞吗?那和兴趣爱好可不一样,你知不知道那有多苦?脚趾变形、韧带撕裂都是轻的!
他的声音带着气急败坏的劝阻,试图用残酷的现实将她拉回“理智”的轨道。
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荆棘密布的绝路。在他眼里,安安稳稳地待在平行班考上一个普通的高中,才是她最明智的选择。
阮绵绵看着他眼中那份混合着震惊、质疑、担忧甚至有些愤怒的情绪,看着他因为急切而微微涨红的脸,心里反而更加平静,也更加坚定。
她清晰地看到了那条路的艰难,但那份被池嘉澍的名字点燃的、名为“不甘”和“渴望”的火焰,已经彻底吞噬了所有对安逸的留恋和对“不可能”的恐惧。
“我知道苦,知道难,知道希望渺茫。”她的声音很轻,却像淬火的钢铁般坚硬,每一个字都带着孤注一掷的重量,“但我没得选。这是我能抓住的,唯一能靠近那里的绳索。再苦,再难,我也要走下去。文化课,我会一分一分地抠。芭蕾,我会一滴滴汗水、甚至一滴滴血地去练。”
她说完,不再看肖怀宇,转身一步一步地离开了公告栏前这片喧嚣之地。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纤细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绝的韧性和决绝。
肖怀宇僵在原地,仿佛被施了定身咒。他脸上的震惊尚未褪去,眼神里充满了茫然和一种……巨大的、被抛下的恐慌。
他看着她决绝离去的背影,看着她瘦小身躯里迸发出的那股近乎悲壮的决心,刚才那番自以为是的劝阻,此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初三分班后的日子平行班的课堂节奏相对平缓,但对目标直指市一中芭蕾特招的阮绵绵而言,每一分松懈都意味着与那遥不可及的目标更远一步。
她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弦,白天在教室,傍晚在舞蹈房,深夜也不停的写题。
苍白的面色、浓重的黑眼圈、偶尔因脚趾剧痛而微微蹙起的眉头,都成了她的日常。
周五放学的铃声终于响起。阮绵绵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教室,脚趾在芭蕾训练后依旧隐隐作痛,让她走路的姿势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僵硬。她正低着头思考刚刚的数学题,一个身影挡在了面前。
阮绵绵抬头。肖怀宇斜挎着书包,站在夕阳的余晖里。他换下了校服外套,穿着一件干净的休闲T恤,额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轮廓分明的脸上带着一种刻意为之的“随意”。
他目光飞快地扫过阮绵绵苍白的脸色和眼底的倦意,又迅速移开,像是怕被她发现自己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