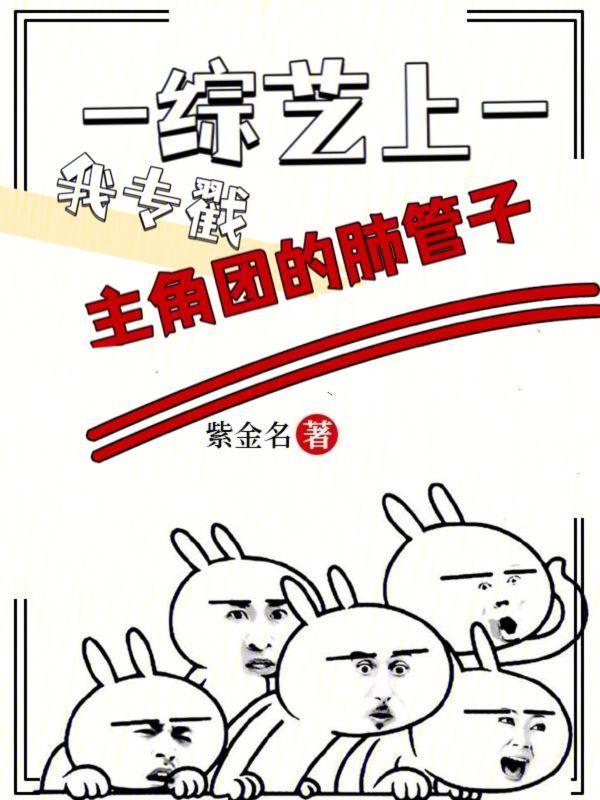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环佩之声是什么意思 > 秋坟鬼唱吊香魂1(第1页)
秋坟鬼唱吊香魂1(第1页)
谢羲和死而复生的地方,名为榕山,隶属四屏郡清平县。
这榕山是清平县中寻常百姓祖祖辈辈的墓葬之地,荒草萋萋,坟茔叠叠。此刻夜深人静,唯有风声呜咽、野草虫鸣。
陶云倦持剑在前开路,剑锋扫过之处,丛生的荆棘与野草伏倒,勉强清出一条可供人通行的小径。
越往深处走,那凄楚的呜咽声愈发清晰,忽然,陶云倦脚步一顿,低声道:“师父,是个妇人。”
谢羲和道:“你再仔细看看。”
陶云倦再看,那扑在坟前哀哀哭泣的妇人,在满月之下竟也不见半点影子,“原来是个守尸鬼。”
人有三魂:天魂归天,乃修行者所称之元神;地魂入酆都,等着孟婆汤生效轮回转世;而人魂,亦称守尸鬼,往往滞留于墓地坟茔,徘徊不去。
那妇人的坟堆甚是潦草,几乎与邻近的荒坟连成一片,显然是仓促下葬,坟头空荡荡的,可见她必然是个没人祭拜的可怜鬼。
谢羲和缓声道:“她无人祭祀,魂魄无依,本就难散,而我的两仪阵是至阴之阵,这才意外助她显形。”
陶云倦走上前,在那沉浸于悲痛、恍然未觉的妇人眼前挥了挥手。那妇人被突然出现的生人惊动,抬起泪眼模糊的脸,吓得魂体一颤,失声叫道:“鬼、鬼啊!”
陶云倦平静道:“你仔细想想,我们是人,你才是鬼。”
妇人闻言一怔,幽暗混沌的思绪仿佛被这句话点明,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虚实难辨的手掌,又望向身前冰冷的坟土,喃喃道:“是了…是了……我已经死了……”
那妇人哭声哀切,字字血泪,语无伦次,谢羲和渐渐从那断续的诉说中拼凑出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悲剧。
这妇人唤作王秀,十指常年缠绕丝线,眼底却从未见过清平县外的天地。后来,王秀嫁了同村的秀才,婚后未满一年,丈夫便上京赶考,也不知是不是路上得了急症还是遇上匪盗,从此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彼时她已有了身孕,不久后便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王香。王秀一人生活本就艰难,又多了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从此更是熬更守夜地绣花,眼睛渐渐坏了,但她心却还未死,总想着把女儿拉扯大,日子就会有个盼头。
王香没有辜负母亲的期待,平安健康的长大了,难得的是她出落得水灵俊秀,天生一副好容貌,被人夸得多了,也渐渐生出了别的心思。
她心气高,不甘于像母亲一样当个绣娘劳碌一生却贫贱一辈子。她自己偷偷学了些字,平日里靠做绣娘维持生计,心里却飘着绮梦,只望有一日能攀上高枝,做人上之人,从此带着母亲摆脱这苦命日子。
后来有一阵,郡里绣坊闹罢工,绣好的布没人来收,王香拿着绣品去郡里散卖,没想到遇见一个路过的富家公子,见她颜色生得好,言语间又有些识见,便甜言蜜语,许下诸般诺言,花言巧语哄骗了她。
王香只道得遇良人,以为终身有靠,轻易托付了身心。谁知那公子薄幸,一朝玩腻便扬长而去,挥挥衣袖连个影子也没留下。
王香失了清白,又遭弃如敝履,在乡邻间受尽白眼。她在家中闭门不出,终日以泪洗面,形容枯槁。王秀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她这一生,所有的依仗和懂得,都系在指尖那一根细小的绣花针上,能绣出贵人手中的富贵牡丹,却绣不出女儿想要的锦绣前程。
她性格温吞甚至有些怯懦,王香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她却并不了解她。
王秀有心想劝,翻来覆去却只有“想开些”、“日子总要过”这几句干巴巴的话;她想护,但自家那单薄的柴门哪里挡得住刺骨的流言和目光。
她只能守着、陪着掉眼泪,看着女儿一日日消瘦下去,一颗心如同被放在绣架上,被无形的针密麻麻地刺穿。
过了些时日,王香决定离开。她听不进母亲劝她本分留家做绣娘的话,也无法将那些刺耳言语当作耳边风,执意离开了清平县这个伤心地,去了邻近的郡城谋生,指望着能重头再来。
数月后,当王香再回家时,王秀几乎不敢认了。女儿身上那股死气沉沉的颓唐不见了,虽清瘦了些,衣裳也仍是旧衣,但脊背挺得笔直,眼里有了光亮,手脚利落,竟似比往日更有主见。
她告诉王秀,自己加入了一个叫“同心会”的地方,那里尽是些同病相怜的女子,姊妹间互帮互助,一同做活计,谁也不轻贱谁。
“孟会长和姐妹们待我极好,教我识字算数,说女子唯有自强,方能不被人欺。”王秀见女儿重拾生气,言语也豁达了许多,心里自是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