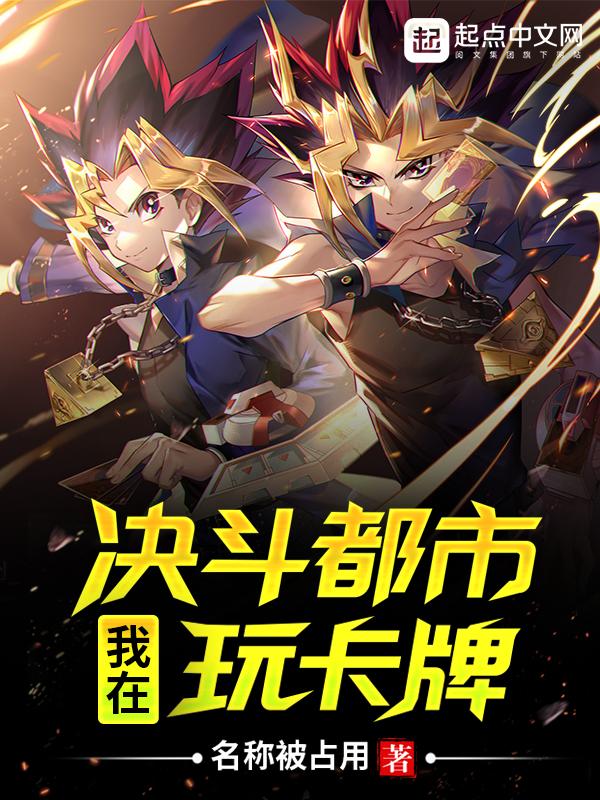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旧域怪诞 > 第二百七十八章 702局(第1页)
第二百七十八章 702局(第1页)
不大的石洞内,随着对方心生怀疑,张文达三人跟来人的气氛变得非常的剑拔弩张。
眼看着因为对不上对方的暗号,即将再次动手的时候,这一刻胡毛毛忽然开口了。“1击,2练。”
这话一出,那男人瞬间情。。。
风停了,但山谷里的蓝花仍在发光。那光不似月色清冷,也不像火焰炽烈,而是一种从内部缓缓流淌出来的温柔,像是被谁轻轻吹亮的烛芯,在夜幕下静静呼吸。孩子们的笑声散去后,花园恢复了寂静,可那朵被摘下的蓝花却没有枯萎,反而在孩子手中越发明亮,花瓣边缘泛起淡淡的金纹,仿佛承载了一段不肯消散的誓言。
陈默仍坐在屋檐下,膝上的日志本微微发烫。他没急着打开??这些年,他已经学会等待。有些话必须等到世界安静下来才能听见,就像雨后的泥土会突然冒出菌丝,无声无息地连接整片森林的根系。
许久,他才缓缓翻开封面。新的字迹正一寸寸浮现,墨色深得近乎紫黑,像是用血与记忆混合书写:
>“声音开始的地方,也是谎言终结之处。”
>“下一个信号源来自北方冻土带。那里有一座沉入冰层的旧电台,每到极夜时分,就会自动播放一段没有署名的天气预报。播报员的声音是女性,语调平稳,却总在‘气温:零下三十七度’之后多说一句:‘别怕,我在等你回家。’”
>“这座电台从未列入国家通信网络,但它影响了方圆五百公里内所有收音机的频段。最近三个月,已有十七人因听到这段广播而徒步走向冰原深处,再未归来。”
>“他们留下的最后影像中,都握着一朵未融化的蓝花。”
陈默闭上眼。他知道那种感觉??当一个声音穿越生死、时间、理性,直抵灵魂最脆弱的角落时,人是无法抗拒的。小树用信件维系母爱,林秀兰用沉默封存悔恨,而这个未知的女声,或许正用一场永不结束的播报,对抗整个世界的遗忘。
他起身进屋,取出背包,将共感增幅器、备用电池、红外套一一检查装入。炉火早已熄灭,但他记得晓花曾说过:“真正的共感不需要设备,只需要一个人愿意听见另一个人的存在。”
临行前,他在小树苗旁蹲下,指尖轻抚那朵七瓣花。“我去看看另一个不说再见的人。”他说。花蕊微颤,露珠滑落,像是一声应答。
七小时后,飞机降落在西伯利亚边缘的科考补给站。寒风如刀,刮过铁皮屋顶发出呜咽般的啸叫。站内人员见到陈默出示的净频局旧证件时,神情复杂。“你是第十四个来找她的人。”值班员递来一杯热茶,“前十三个,都没回来。”
“你们知道那个声音是谁?”
“不知道。但我们监测到,那段广播只在特定共感频率下才能接收到。普通人听只是杂音,可一旦有过‘重要之人离去而未能告别’的经历……就会听得清清楚楚。”
陈默点头。“所以那些人不是失踪,是回应了召唤。”
他租了辆雪地摩托,带着导航仪和保温舱出发。地图上,那座废弃电台位于一片被称为“静默三角”的区域??卫星信号常年中断,指南针失灵,连候鸟都会绕道飞行。越是接近,增幅器的读数就越紊乱,直到最后,屏幕上只剩下一行不断跳动的数字:**共感密度:98。7%**。
夜幕降临,极夜正式开始。太阳已连续四十天未升起,天地间唯有雪反射的微光。远处,一座倾斜的铁塔破冰而出,天线断裂,控制室半埋于冻土之中。门口积雪堆成奇异的弧形,像是有人年复一年清扫出一条通往室内的路。
推门瞬间,暖意扑面而来。
这不可能。
这里不该有任何能源维持供暖。
室内整洁得诡异。桌上有冒着热气的咖啡,墙上挂着一件厚呢大衣,炉子上炖着土豆汤,咕嘟作响。一台老式磁带录音机正在运转,转轴缓慢旋转,传出那段熟悉的广播:
“这里是北纬78°12′,东经104°03′临时气象站。当前时间:极夜第113天。天气状况:晴,风速三级,能见度良好。气温:零下三十七度。别怕,我在等你回家。”
声音温润,带着一丝沙哑,像冬夜里母亲低语。陈默站在门口,忽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某种深层记忆被强行唤醒的撕裂感。他踉跄几步,扶住墙壁,眼前闪过画面:一个女人披着军绿大衣,在暴风雪中回头望他,嘴唇开合,却发不出声音;一辆雪橇翻倒在冰沟里,上面绑着一只褪色的布熊;还有……还有一句没能说完的话:“答应我,别忘了……”
“你想起来了?”
声音从身后传来。
陈默猛地转身。
女人站在阴影里,面容模糊,轮廓却被蓝光勾勒得清晰。她穿着旧式气象员制服,胸前别着一枚锈迹斑斑的铜牌,编号:X-09。
“你是……”
“苏婉。”她说,“1978年派驻此地的首席观测员。也是你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