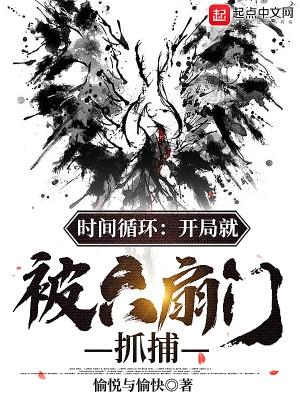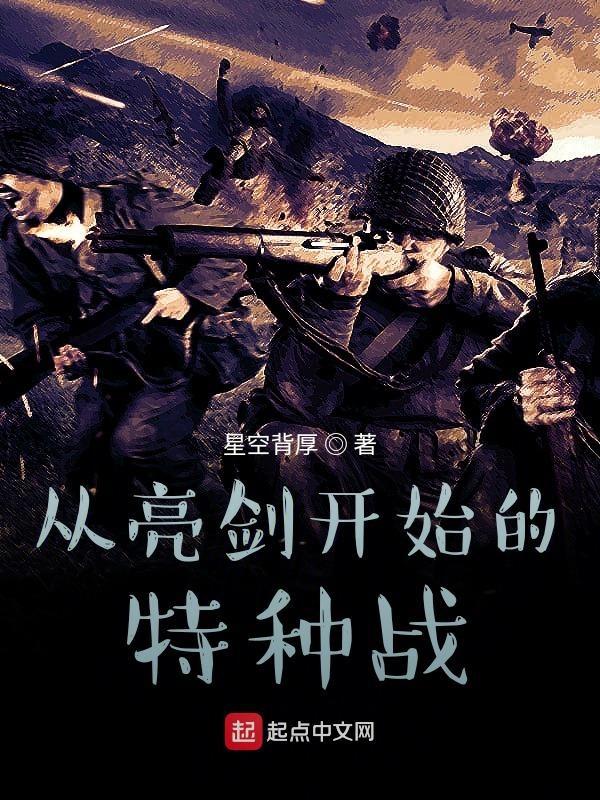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从岭南孤女,到开国帝王 > 州试一(第2页)
州试一(第2页)
在她附近,竟无一合之敌!
看着竞争者们的窘状,姜渺心情大为愉悦,干脆起身,将答卷刻意抖了抖,才奉到刺史、太守和县令三人面前。
经常考试的朋友们都知道,在考试时最忌讳的就是,自己还在找思路的时候别人已经答完了。众考生看见姜渺起身交卷,心态瞬间就崩溃了。
考场上顿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杂音,吸气者有之,研墨者有之,咬牙暗骂者亦有之。
青袍县令起身道了声肃静,眼见更香才烧了一半,不由心里泛起了嘀咕。但他知道眼前这人是刺史开了口放进来的,写的好坏与否都轮不到他来评判,因而接过卷子就转递到王刺史面前。
王刺史低头才看了一瞬就立马闭上眼睛,他有些后悔之前让她进场一试了。这时候做官讲究个“身言书判”,其中“书”指的就是书法功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家都默认文章写得好的人,书法一定也不会差。像姜渺的师父王临,论书法一道在当今就能排进前三。
反之,像姜渺这样的蒙童字迹,不用看就能知道文章会是什么成色。所以王伯渊是怎么教出个这样的弟子的?还是说,这人真的是个骗子?
见王刺史闭目不语,青袍县令和张太守两人一左一右地瞥了眼卷子,顿时心中有数,看来使君是被那小丫头给糊弄了。
张太守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让姜渺入内,因为陈肃一开始是将举荐信送到他这儿被否了的。可没想到陈叔敬宁愿冒着前程受阻的风险也要越级举荐这丫头。她又偏偏运气好,拜了琅琊王氏子弟为师,还正好入了使君的眼。
种种巧合之下,才让姜渺有了入场考试的资格。不过现在看来,倒也不是件坏事。待使君验过这丫头的成色后,就不会再固执己见了,到那时,自己说不得还得劝劝使君不要太大动肝火才好。
王刺史自然不晓得张太守心中的小九九,他深吸一口气,还是睁开眼准备耐着性子读一读。暗自盘算,只要她的文章有一点可取之处,就给判个中上,等第二场考算学时再把她刷下去,既给足了王伯渊面子,也免得有人说他识人不明。
他打定了主意,这才勉强将目光投向面前的卷子,一目十行地快速浏览着。第一道贴经题不出意料的是全对,王刺史眉头舒展些许,要是第一道就错了,他还真没办法腆着脸给人判过,过不去自己心里那关啊。
再看第二道,嗯?怎么写了这许多字?
王刺史耐心看了两行,顿时端正了坐姿,眼神专注,再往下看去,就变得神色欢悦起来。若不是顾忌着身在考场,他简直要拍案叫绝!
张太守和县令二人看见他的神情变化,心中诧异,也都凑近细细观看起来。
两人俱都看完后,竟罕见的齐齐陷入沉默。
左右对视一眼后,还是县令沉吟着开口:“礼之本在于敬,乐之本在于和。全篇以敬、和二字用的最妙。”
张太守有些不愿意承认,勉强道:“不过是拾人牙慧,前一句摘自《孝经》,后一句摘自《礼记》,也无甚稀奇。”
王刺史和县令动作一顿,俱都向他看来。
不过是拾人牙慧?你可要点脸吧!
题目问的的《论语》,她却能另辟蹊径,想到化用《孝经》和《礼记》中的句子变成自己的观点,再用来阐释问题,这说明什么?第一,她脑子灵活,能以常人想不到的角度答题;第二,她至少已经贯通三经,对这三部典籍都有深入的钻研理解。
按照先前的举荐文书中所说,这女娃的家世勉强只算得上的寒门,拜王伯渊为师也没有多少时日。除了感慨不愧是琅琊王氏,培养人才有一手外,就只能说姜渺此人实在天资卓绝了。
王刺史捋着胡须展颜笑道:“如此文章,我欲定为上上,汝二人以为如何?”
青袍县令第一个出言附和,张太守也只能尴尬地笑笑,点头答应。
不服不行啊。
张太守看着姜渺,眼中闪过一丝厌恶。本来好好的安排,都被这个不规矩的丫头给毁了。
且让你得意一时,第二场算学可就没那么容易过了。
张太守在心中想到。这第二场的考题是他找了精于此道的下属出的,为的就是将绝大多数考生拦在门外,好让花了钱,早早和他疏通了关系,提前得知了题目和答案的富户子弟一举得中。
他本来也不想做这等下作之事,只是,他给的实在太多了。既然钱货两讫,那就只好拿人钱财,与人方便了。
这场州试三场考试只录一人,若是那丫头第二场答不上来交了白卷,任她将文章作的再花团锦簇,使君也不好徇私,将她直接取中吧?
退一万步来说,他只是默许了泄题,又没保证一定让那孩童取中。要是有了优势还取不中,这就是自己能力不行,与他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