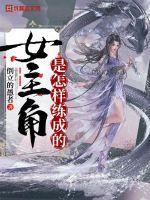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红楼]女驸马 > 风骨与头脑一热(第2页)
风骨与头脑一热(第2页)
只是这“小吏”二字,到底是过谦了。
于这大周朝堂之上,“官”与“吏”二字,虽一字之差,却有云泥之别。
官者,朝廷之栋梁,庙堂之器也。
他们或由科举正途出身,十年寒窗,一朝得中,天子门生,身负经纶济世之任;或承祖上荫庇,门阀贵胄,生而便在云端。
官有品阶,有俸禄,有升迁调转之途。
官,是政策的制定者,是风云的搅动者,一言可安邦,一语可定国。其位在朝,其名在史,是为“士大夫”。
而吏者,多不涉科举,或由本地遴选,或为世代相承。吏无品阶,仅凭簿书文书为生,终其一生,或许都固守于一府一县。
吏是律法的执行者,是俗务的操办者,日日与案牍劳形,与百姓打交道。官如流水,过一任便换一地;吏如磐石,根植于乡土,盘根错节。
故而,一个“官”字,代表着身份、荣耀与前途;一个“吏”字,则意味着卑微、劳碌与局限。
湘云乃是今科新点的探花郎。
探花者,天下读书人的第三,一入仕途,便可入翰林,为天子近臣,未来更是宰辅之才,是“官”中最清贵、最被看好的那一类人。
此刻,她对着三皇子,自称为小吏,将自己置于最微末的位置,既表达了对上位者的无限敬重,又消解了可能因才名而招致的猜防。
这自谦,在三皇子眼里,非但不会折损她探花郎的半分身价,反而更显得气度从容,不矜不伐。
端的是不掩清华,反见风骨。
三皇子笑了,将手中玉杯放下,看了她一眼,笑着说:“史爱卿是明白人。”
他说“明白人”三字时,眼神温和,像是真心欣赏她的言辞谨慎。
他略略俯身,离她近了些,低低地说:“既是明白人,就该晓得良禽择木的道理。我那位好父皇……他看人的眼光,有时候可不大济事。”
这话说得轻描淡写,却是不敬,只因出自皇子之口,反倒添了几分纵容娇惯的意味,像被宠坏了的幼子撒娇抱怨。
若是不细思,或许只当他是个心直口快、会说笑话的闲散王爷。可史湘云心里却是一凛。
能在圣上膝下如此放肆抱怨的人,要么是真糊涂,要么就是笃定有人护着他,无人敢拿他这几句话做文章。
三皇子的目光又飘向不远处正与武将们高声谈笑的尔朱豪,话里满是轻蔑:“不过是一介武夫,空有匹夫之勇,不知礼义,不通文墨。若是将宝压在此等人身上,怕是最后连怎么输的都不知道。”
没有点名道姓,是皇家权谋里的心机和体面。
但湘云和他,都明白在说尔朱豪,又隐隐指向太子李承宇,那位将尔朱豪捧到殿前、借以自重声势的储君。
既是在贬低尔朱豪的粗鄙,更是在暗讽太子识人不明,甚至……隐隐指向了那位高坐在龙椅上、偏宠武将的帝王。
史湘云并未接话。
她脑中却不由自主浮出皇后的影子。
如今坐在她对面的,是皇后最得意的儿子,温润如玉,笑谈之间便要试探她站在何处。
这天家兄弟的嫌隙,她一个小小的翰林官,可不想沾。
【宿主,别听这三皇子画饼。他自己年纪一到可是要就藩的,还想拉你上船。听听这酸味,啧啧,妥妥是在嫉妒他爹更喜欢那个只会打仗的尔朱豪。】
史湘云正暗自思量。
席间笙歌渐歇,只余曲终人散前的一点余韵。
风从曲折游廊外吹入,带着新酿桂花酒的清气与海棠、牡丹混作一处的幽香。
彩绣帷幕轻轻鼓起,又慢慢落下,将诸般笑语滤得有若隔帘看花一般,朦胧。
念头正乱,面前却一暗。
湘云心中一凛,眉头才微一蹙,抬眼,只见那壮硕的尔朱豪不知何时已走到跟前,正朝她抱拳。
“末将尔朱豪,见过史探花。”
他这一抱拳,袖底肌肉虬结,连锦袍下衣纹都略略绷紧。
口中虽称“末将”,姿态却极稳,眼神更如明枪直刺,含着一股江河奔涌之势。
言语之间倒是颇为客气,只是这等客气,亦可能是先礼后兵。
三皇子一挑眉,却是不语。明显是抱了看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