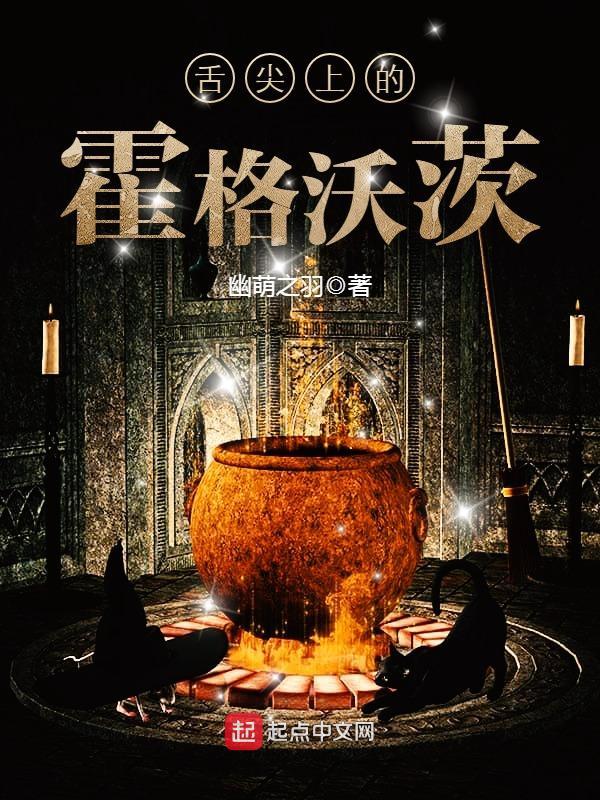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韫玉 > 第 167 章(第1页)
第 167 章(第1页)
油灯如豆,简陋的土屋内,光线昏暗。盛暄的呼吸声很快变得均匀绵长,显然白日奔波劳碌,已然沉沉睡去。
苏泽兰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却毫无睡意。他睁着眼,望着被烟火熏得发黑的低矮屋顶,耳边似乎还回响着白日的徒劳、村民避之唯恐不及的低语、以及孩童那句无心的“鬼住的地方”。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在他紧绷的神经上反复刮擦。
那条通往痛苦源头的路,在黑暗中似乎显现出了一丝微弱的轮廓,却也更让他心绪难平。对真相的渴望、对残酷过往的恐惧、以及近乡情怯般的巨大悲伤,如同潮水般反复冲击着他,让他无法安宁。身体疲惫到了极点,精神却异常清醒,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在寂静中擂鼓般跳动的声音。
他极力克制着翻身的冲动,生怕惊扰了身旁的盛暄,只能僵硬地躺着,任由纷乱的思绪在黑暗中肆虐。
就在这时,一只温热而沉稳的手掌,轻轻落在了他紧绷的肩头上。
苏泽兰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微微一颤。
那只手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安抚性地轻轻拍了两下,动作沉稳而带着奇异的安抚力量。紧接着,萧祈昀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在身侧响起,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怕打破了夜的寂静,却清晰地传入苏泽兰的耳中:
“别想了。”萧祈昀的声音里没有责备,也没有过多的情绪,只有一种洞悉一切的沉稳,“既有线索,明日循迹去找便是。此刻辗转反侧,于事无补,徒耗精神。”
苏泽兰沉默着,没有立刻回应,但肩头那绷紧如铁的肌肉,却在萧祈昀沉稳的掌温下,几不可察地松弛了一点点。
萧祈昀的手并未离开,依旧稳健地按在他的肩头,仿佛要将自己的力量和冷静透过掌心传递过去。“闭上眼睛,放缓呼吸。”萧祈昀的声音继续低低地响起,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引导意味,“养足精神,明日才有力气应对。”
苏泽兰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依言闭上了干涩的眼睛。黑暗中,肩头上那只手的温度和重量变得格外清晰,像是一座沉默而可靠的山峦,镇住了他几乎要失控的心潮。
萧祈昀没有再说话,只是保持着那个姿势,无声地传递着安抚与力量。
时间在寂静中缓缓流淌。苏泽兰努力摒除杂念,将注意力集中在肩头那沉稳的触感和自己逐渐放缓的呼吸上。激烈的心跳慢慢平复,紧绷的神经也一点点松弛下来。极度的疲惫终于战胜了纷乱的思绪,沉重的眼皮缓缓合上,呼吸逐渐变得均匀而绵长。
在他彻底陷入沉睡的前一刻,似乎感觉到肩头上的手掌极其轻柔地又按了一下,然后才缓缓收回。
黑暗中,萧祈昀静静地侧卧着,听着身旁两人逐渐同步的平稳呼吸声,深邃的眼眸在昏暗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微光,随后也缓缓闭上了眼睛。
简陋的土屋内,终于彻底安静下来。窗外风声依旧,却不再显得那么凄冷刺骨。这一夜,苏泽兰在沉重的期待与不安中,最终在萧祈昀沉稳的守护下,寻得了一丝短暂的安宁,沉沉睡去。
天光微熹,薄雾笼罩着这个偏僻的小山村。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泥土的气息,远处传来几声零星的鸡鸣犬吠。
三人早已起身。苏泽兰的脸色依旧带着一丝疲惫的苍白,但眼神却比昨夜清明了许多,那簇微光在眼底沉淀下来,化作一种更加沉静的坚定。他仔细地将那个小小的包裹重新系好,贴身收好,动作间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郑重。
盛暄精神抖擞地收拾着简陋的行囊,一边絮絮叨叨:“这土炕睡得我腰酸背痛……不过总算有眉目了!苏泽兰,你放心,今天肯定能找到!”
萧祈昀则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他已将马匹备好,正站在院中,目光投向昨日孩童所指的那条荒芜小径的方向,深邃的眼眸中带着惯有的审慎与考量。
简单的洗漱用过早饭后,萧祈昀从行囊中取出一些铜钱,放在主屋那张破旧的木桌上,算是酬谢。那家主人,一位老实巴交的农妇,推辞了几下,最终还是千恩万谢地收下了。
苏泽兰走到院门口,对着那农妇微微颔首,声音平静:“多谢。”
农妇看着他清俊却难掩风霜与某种沉重气息的脸,又看了看他身后气质不凡的盛暄和萧祈昀,嘴唇动了动,似乎想再劝些什么““莫要去”的话,但最终还是化作一声叹息,只是低声念叨着:“几位……路上千万小心呐……”
苏泽兰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再次点了点头,转身走向已经牵马等候的盛暄和萧祈昀。
盛暄利落地翻身上马,朝着那条荒草萋萋的小径扬了扬下巴:“是这条路没错吧?苏泽兰?”
苏泽兰翻身上马,坐稳后,目光锐利地扫过那条蜿蜒消失在晨雾和山林深处的小路,昨日孩童的话语和模糊的记忆碎片在脑海中交织。
他深吸一口气,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是,走吧。”
他一抖缰绳,率先策马踏上了那条荒芜的小径。马蹄踏过及膝的荒草,发出窸窣的声响,露水打湿了马腿和衣袍下摆。
盛暄立刻策马紧跟而上,口中还在说着:“我在前面开路!这草也太深了……”他拔出腰间的佩刀,挥砍着过于茂密的枝杈和藤蔓,为后面开辟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