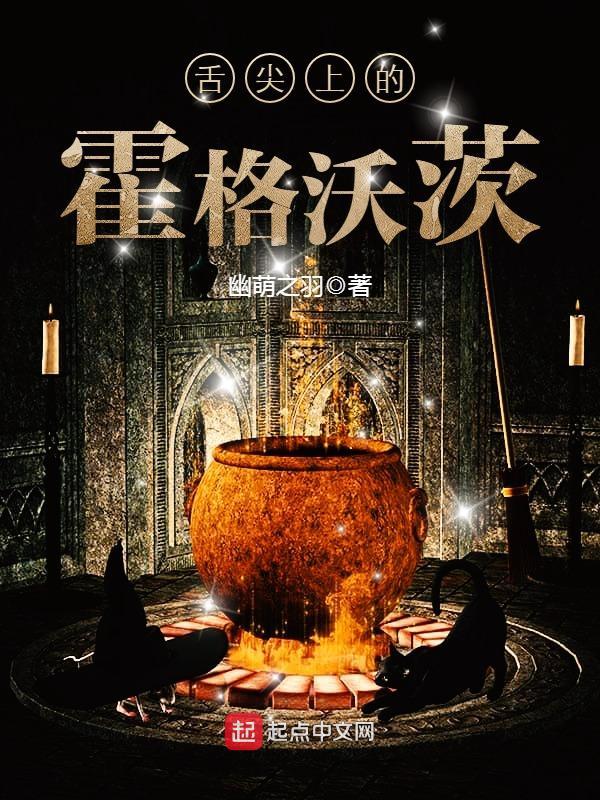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韫玉 > 第 167 章(第2页)
第 167 章(第2页)
萧祈昀则沉默地控马断后,他的目光始终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的环境,留意着任何可能的危险迹象,同时也将苏泽兰那挺直而决绝的背影收入眼底。
三人沿着这条几乎被遗忘的小径,向着那片被当地人视为禁忌的、笼罩在晨雾中的黑沉沉山峦深处行去。晨光艰难地穿透雾气,在林间投下斑驳的光影,四周寂静得只剩下马蹄声、盛暄挥刀砍断荆棘的声响,以及远处不知名鸟类的孤鸣。
苏泽兰的目光紧紧盯着前方,每一个转弯,每一处地貌特征,都与他脑海中那些被痛苦尘封已久的碎片进行着比对。他的心脏在胸腔中沉重地跳动着,既有即将触及真相的迫切,也有面对残酷过往的凛然。
三人沿着那条荒芜的小径,在愈发崎岖的山林中穿行了近一个时辰。晨雾彻底散去,阳光变得刺眼,却驱不散这片山林深处弥漫的、越来越浓重的死寂与荒凉气息。
空气中开始隐约飘来一丝若有若无的、混合着陈年焦糊味和腐朽气息的味道。苏泽兰的脊背绷得越来越紧,握着缰绳的手指因为用力而骨节发白,但他的目光却始终锐利地扫视着前方,不曾有丝毫动摇。
终于,在绕过一片茂密的、几乎将小路完全遮蔽的荆棘丛后,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却又瞬间将人拉入一种令人窒息的荒芜与死寂之中。
那是一片开阔的山坳。谷底,大片焦黑的断壁残垣如同狰狞的伤疤,沉默地匍匐在疯长的荒草与灌木丛中。房屋的轮廓早已模糊不清,只剩下高低错落的、被烟火熏得漆黑的石头地基和零星几根倔强指向天空的焦黑梁柱。一条早已干涸龟裂的河床,如同死去的巨蟒,蜿蜒穿过废墟的中心。目之所及,尽是破败、倾颓与一种被时光和灾难共同遗弃的苍凉。
没有鸟鸣,没有虫声,甚至连风似乎都刻意绕开了这片土地,只有一种沉重的、令人心悸的死寂。
苏泽兰猛地勒停了马。
他端坐在马背上,身体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一动不动。深邃的眼眸死死地锁着那片废墟,瞳孔剧烈地收缩着,仿佛要将眼前的每一寸残酷都刻入灵魂最深处。
没有惊呼,没有泪水,甚至没有明显的颤抖,只有一种近乎凝固的、冰封般的死寂笼罩着他。但那冰封之下,是汹涌澎湃、几乎要将他撕裂的滔天巨浪——刻骨的恨意、沉痛的哀伤、以及一种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彼岸的、冰冷的确认。
“……是这里。”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如同砂纸摩擦过粗粝的岩石,每一个字都带着千钧的重量,砸在寂静的空气里。
盛暄和萧祈昀也相继勒马停在他身侧。盛暄看着眼前这片惨烈的废墟,倒吸了一口凉气,脸上写满了震惊与不忍,他下意识地看向苏泽兰,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紧紧攥住了缰绳。
萧祈昀的目光锐利地扫过整片废墟,评估着环境,最终落回到苏泽兰那仿佛凝固住的侧影上,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情绪。
苏泽兰沉默地凝视了片刻,然后,他极其缓慢地翻身下马,动作有些僵硬,双脚落地时,仿佛踏入了某种无形的泥沼,沉重而滞涩。
他依旧紧紧抱着那个包裹,一步一步,朝着那片埋葬了他所有温暖与欢乐、也吞噬了他至亲生命的焦土走去。
步伐缓慢,却异常坚定,仿佛每一步都踏在仇敌的骸骨之上,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决绝。
盛暄和萧祈昀对视一眼,立刻翻身下马。盛暄迅速将三匹马的缰绳拴在旁边一株枯死的老树树干上。
萧祈昀则快步跟上苏泽兰,保持着一个既能随时伸手扶住他、又不会过度打扰的距离。
苏泽兰没有回头,他的全部心神似乎都已投入了眼前的废墟。他穿过齐腰深的荒草,踩过破碎的瓦砾和焦黑的木炭,目光如同最精准的尺,丈量着这片早已面目全非的土地。
最终,他在一片相对开阔的、依稀能辨认出院落轮廓的废墟前停了下来。
那里曾经或许有一圈低矮的石墙,如今大部分已经坍塌,被荒草和泥土掩埋。院内,几处焦黑的地基轮廓依稀可辨,其中一处相对较大,旁边还散落着一个被砸得变形的铁锅和半截烧焦的磨盘。
苏泽兰静静地站在那残破的院门口,身影在广阔的废墟和苍白的天空映衬下,显得异常单薄而孤寂。他久久地凝视着院内,仿佛能透过这片狼藉,看到昔日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的景象。
那些被刻意尘封的、最温暖的记忆,与眼前最残酷的现实猛烈碰撞,几乎要将他击垮。
他的身体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
一直紧随其后的萧祈昀,立刻不动声色地向前半步,手臂微微抬起,形成了一个无声的、稳固的支撑。
盛暄也紧张地屏住了呼吸,拳头捏得死紧,却不敢贸然上前打扰。
苏泽兰深吸了一口气,那气息带着浓重的焦土和腐朽的味道,刺入肺腑。他最终抬起了仿佛重逾千斤的脚,迈过了那道早已不复存在的门槛,踏入了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