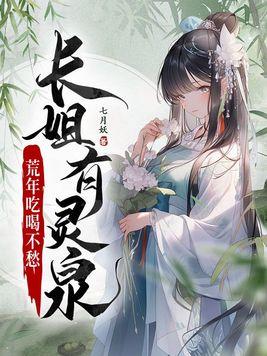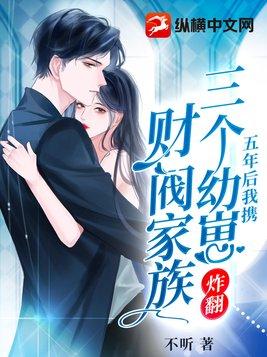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 > 三个体性哲学自我的显明 (第1页)
三个体性哲学自我的显明 (第1页)
三、个体性“哲学自我”的显明:
哲学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自由和启蒙精神的捍卫和深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哲学思想者和研究者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哲学思想者和研究者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哲学的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自由与启蒙精神得以彰显的重要表现之一。
(一)代表“我”的“我们”:个体性“自我”的隐匿
真正创新性的哲学思想首先是个人的创造,然后才谈得上对他人的影响并具有“社会历史意义”。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是实现哲学自觉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的哲学研究者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需要追问与反思的问题。在哲学的理论著述中,经常可以看到,每当作者在表达自己观点时,经常习惯于使用“我们认为”、“在我们看来”、“我们觉得”、“我们强调”、“我们发现”、“我们赞成”、“我们反对”等字眼。明明是“作者个人”在“想”和“说”,可为什么他偏偏不用“我认为”、“我承认”、“我发现”、“我希望”等而非得用“我们”来代表“我”?
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仅是一种语言使用的习惯?
这的确是一种语言使用习惯。但按照精神分析学说的说法,所有语言习惯,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都蕴含着潜意识的深层欲望。而且不仅如此,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还可发现,事情可能包含着更为丰富和复杂的意义。
首先不难发现的是,用“我们”来代替“我”,这是一种“怯场”的表现和“自我保护”的措辞。心理学家早已指出,独自一人面对众人发言讲话,大多数人都有难以克服的恐惧心理,把“我”无遮拦地暴露和呈现在人们面前,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心理学家同时指出,只要有充分的准备和自信,这种恐惧心理是完全可以战胜的,那些优秀的演说者即是明证。因此,用“我们”来代表“我”,除了心理原因,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原因,那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认同与学术“道统”中,很少把理论观点、理论创造、理论发现与普通的、个体性的理论思考者和表达者联系起来,而是把它们视为普通的生命个体没有“资格”和“能力”承担的“神圣事业”。很显然,这在根本上是中国几千年“群体本位”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学术理论上的具体而微的表现。在此传统的支配之下,人们相信,只有特选的“神圣人物”才有资格和权力进行理论创造、提出创新性的理论思想、做出重要的理论发现,因而也只有他们拥有特权,可以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论,因此,古代的圣人可以用“子曰”来对芸芸众生进行教导,经典作家和领袖人物可以用个人身份和口吻发言,国外的哲人可以用“自我”的声调和姿态出场,与此相对,普通民众的主要责任是“倾听”与“接受”,普通哲学学者与理论研究者的主要工作是“阐发”和“注解”,至多是“照着讲”和“接着讲”。在这种传统和“潜规则”的支配之下,理论思考和研究者面临一种尴尬和矛盾的处境,一方面,在个人的思考和研究中,他的确“有话可讲”、“有话要说”;另一方面,他又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担当把“自我”坦呈出来,交付给一个不确定的、可能对自我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可能会带来风险的外部世界。于是,把“我”隐藏在“我们”的面具后面,让“我们”去传达“我”的声音,就成为了一种十分自然的选择。
这表明,在“我们”代表“我”的措辞后面,是“我”向“我们”的屈服,是对“自我”有意识的压抑和逃避。与此相辅相成的,让“我们”来代表“我”,使“自我”也得到了相应“回报”:“理论言说”的“集体主义”成为了隐蔽和保护个人的有效的“护身符”和“保护壳”,“自我”在“我们”的“保护”下获得了“安全感”。个体言说摆脱了责任的重负,一起加入了“我们”的“大锅饭”,同时也为自己撑开了一把“我们”的“保护伞”。
一方面是“怯场”和“自我保护”;另一方面却是“自大”和“自我膨胀”。用“我们”来代表“我”,同时又是一种把“个人”的思想和话语化身为“公共”的思想和话语的修辞策略,它使思想和话语摆脱了“个人言说”的“主观性”而转换扩展为“超个人”的“客观性”论述,并使之获得了某种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和“权威性”。在此意义上,对“个人自我”的隐藏,实质上又包含着一种把“我”的思想和话语权威化与客观化的潜在意志与欲望。
与前述“怯场”和“自我保护”倾向有所不同,这并非中国文化和语境所特有,而是哲学史上屡见不鲜的普遍现象。法国哲学家施兰格在《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一文这样引用笛卡尔的自我陈述:“我戴着假面具出场……上场的演员们为了不让观众看到他们脸红,都戴上一副面具。像他们一样,我在登上这个世界舞台——在此之前我只是观念——时,也戴上假面具出场。”[1]为何要戴上假面具?因为他相信并且要让别人相信,“我”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声音,而且是真理本身的声音。因此,“我”的思想和话语就不能仅仅是个人的言说,而是“我们”都应无条件倾听和服膺的“公共性”真理。
这里的“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指称和置换为不同的内容,例如“家族”、“种族”、“集体”、“阶级”“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等。因此,以“我们”来代表“我”,使得本来是个体性的言说具有了超越个人的“公信力”。因为此时,“我说”、“我认为”、“我想”就获得了“我们说”、“我们认为”、“我们想”等公共性的意义。顺着这一思维逻辑,其思想轨迹很有可能变成这样:由于它是“我们”的观点,因而是体现了“客观规律”与“历史必然趋势”的言说,于是同时也就是所有的人必须洗耳恭听、无条件接受和服从的“真理性叙事”。
这意味着,让“我们”来代表“我”,蕴含着这样的前提性信念:“我”虽然是“个人主体性”,但却可以通过“我们”的代理,获得“主体间”的“客观有效性”。当“我认为”变成“我们认为”,“我想”变成“我们想”、“我承认”变成“我们承认”,“我主张”变成“我们主张”时,“我”的主观性得到了超越和克服,其声音被无限放大,“独唱”成为“合唱”,个人之理成为公共之理,由此给接受者带来这样一种巨大的暗示和压力:这不是某个人的观点,而是人们共同的理论诉求,它体现着“公意”,反映着“客观规律和历史趋势”,因此,拒绝接受它就意味着拒绝某种似乎成为“我们”所“公认”的东西。这即是说,以“我们”的口气说话,意味着一种“客观的语调的运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说话的不是我哲学家,而是真理通过我的嘴说出来,我们都同意真理完全有权力摆权威架子。”[2]为“个人言说”戴上了“客观中立”的“面具”,这就是以“我们”代表“我”来说话带来的特别的修辞效果。
以上两种倾向,一为“自卑”;二为“自大”。它们从两个极端揭示了用“我们”的“公共话语”替代“我”的“个人话语”所隐含的双重含义。这双重含义在表面上正相反对,一为“向后的退缩”,二为“向外的扩张”;一是“自我保护”,二是“自我膨胀”。但正像一个缺乏独立人格的人一样,“自卑”和“自傲”这相互对立的两极往往集于一身,从而形成一种“分裂”的、“双重型”的个性和人格。思想理论的品格亦如是。
(二)个体言说的自觉与理论创新
卸除所戴的种种假面具,显明隐匿在“我们”后面的“思想自我”,自觉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理论言说在根本上只是“个体言说”,这是真正的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
“理论创新”在今天已成为最时髦的字眼。但人们对这种“创新”的最为基本的条件却经常缺乏应有的反思。对于哲学来说,真正的理论创新的重大前提就是从事哲学工作的每个人“自我”的解放与凸显。当我们再三强调“思想解放”与“观念变革”的时候,经常遗忘了“思想解放”最核心的“思想者自我”的解放,“观念变革”最根本的是“思想者头脑”的变革。这是因为,哲学既不能如经验科学一样可以依靠实验等技术手段获取新知识,也不能如形式科学一样依靠先验推理演绎答案,而只能靠每一个人的头脑,创造出“哲学思想”。作为“哲学思想”,其最可贵的品格就在于“推陈出新”、“标新立异”乃至“异想天开”,只有这样,哲学的“创新”才成为可能。因此,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哲学理论创新必然是哲学家“自我”的“个人言说”,必然表达的是他的独特性的“思想”、“意见”、“直觉”、“信念”、“见解”、“论证”,等等,而不能是“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戴着“我们”面具的面目模糊的言说。
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显明隐匿在“我们”后面的“自我”对于理论创新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只有理论“自我”的彰显,才能对“个人言说”与“主义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自觉的划界,并真正守护和捍卫具有创新性的哲学理论所应有的精神品格。
关于“主义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有学者做出了这样的描述和规定:所谓“主义话语”,就是“带价值论断的社会化的思想言论,这些论述以某种知识学(科学)的论证来加强价值论证的正当性,以此促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化行为。……当某种思想话语进行社会化推论和诉求时,或当某种由个体提出的思想论述要求社会法权时,思想论述方转换为‘主义’话语”,而一旦“‘主义’话语获得社会法权,就成为意识形态”[3]。这意味着,“个人话语”、“主义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三种话语形态。
“个人话语”与“个体言说”是哲学思想者个人自由探索和创造的思想成果,它是个人灵魂之镜向外折射或外化的产物,体现的是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人文价值关怀。它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这一个”。哲学史上那些最杰出的哲学家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作家”、其著作之所以被称为“经典著作”,就是因为其或者改变了看问题的视角和眼光,或者重新提出和阐述了问题,或者迫使人们在已经泰然处之、无动于衷之处面对不可回避的重大思想和现实困难,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真正的哲学家和哲学特殊的重大功能,那就是以自由之精神、原创之勇气,不服从于任何既定的教条和权威,努力把人们从种种“正统”学说的束缚和压抑中解放出来,击碎已经过时或即将过时的思想和现实的坚硬外壳,并为思想和生活的未来打开自我超越的空间。对此,伯林的概括十分中肯:哲学在它最有效的时候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变换——而且用这种方式变换的范畴或观念越根本,也就是说越不容易遭到常规自我检省的压抑,我们就认为一种哲学越深刻——它必然是朝着更广泛的自由、推翻现存价值观和习惯、打破界限、改变人们熟悉的特征等方面发挥作用,这令人兴奋又不安”[4]。因此,充满个性的自由创造、不被任何专断力量所同化的叛逆精神、不服从于任何“正统”权威与既定秩序羁绊的超越意识,这是作为“个人话语”的哲学的独特精神品格。
与“个人言说”不同,“主义论述”的根本旨趣却在于谋求对某种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秩序的支配和主宰地位。“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达尔文主义”、“资本主义”、“功利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等,如果去掉“主义”称谓,所有这些价值理念和主张,无论“自由”、“保守”、“资本”,还是“功利”、“科学”、“个人”、“集体”等,在自由、开放、多样化的公共思想空间中,都拥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同样,它们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表达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健全生命存在的憧憬和追求,因而构成具体、全面和丰富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内在环节和内容。但是,一旦成为“主义话语”,就意味着它们每一个把自身都当成体现了“客观规律”和“必然性”的、具有拯救功能的、把所有人带向解放的权威话语,都体现着充当绝对的、无条件的、终极的价值规范基础的诉求。这使得“主义话语”难以摆脱“非此即彼”与“两极对立”的思维定势与思想原则,“排他性”和“独断性”由此成为“主义话语”的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