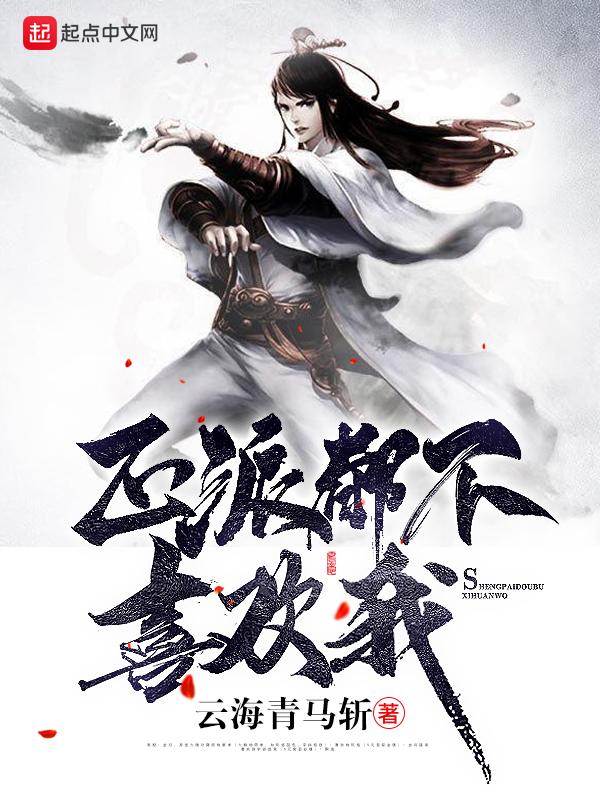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百年变局 > 09 博弈 谁将获取规则霸权(第2页)
09 博弈 谁将获取规则霸权(第2页)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使得西方国家蓦然发现,过去的游戏进行不下去了。因为随着全球产业格局的变迁,“西方7国”(G7)GDP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70%以上下降到了2008年的50%,并且还在快速下降。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新兴市场自己组织起来,不带发达国家玩了”的局面。
于是,2008年美国邀请了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首脑到华盛顿开会,共商应对金融危机大计。这样G7扩展成了G20,世界秩序进入了新的时代。
G20时代是全球化生产的时代,虽然国家间政治上区分彼此,但生产链条却是全球一体,共享同一个微观经济基础。基于一国国内统计的GDP已无法客观描述经济面貌了,由此,各种修正GDP的方案出现了,其中有着重大影响的有三种,每一种方案背后都蕴藏着极深的谋略算计。
第一种是在G20框架下基于“全球价值链”议题的“贸易增加值算法”。其思路是:中国有一半左右的贸易量来自加工贸易,也就是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制成后直接出口,中国企业在该过程中只获得了很少的加工费用,但却在数字上造就了中国庞大的出口量。因此,中国的出口额应该根据“贸易增加值”进行核减。核减后中国的GDP将降低。
第二种是美国进行的GDP统计方法改革。2013年4月,美国宣布将调整GDP统计内容,把研发支出、电影版税等“21世纪的组成部分”纳入。根据这种新算法,企业、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研发费用支出将被视为固定投资,有关娱乐、文学及艺术原创支出也将作为固定投资纳入GDP。经过这种调整,美国1959年至2002年的GDP水平平均提高2。6%至4。6%,其中1995年至2002年增长更是高达6。7%。
第三种最为重要,是联合国框架下推进的“绿色新经济”框架,该框架包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核算,改变只计算经济活动的GDP。评价社会资本的方式是“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体系,衡量“自然资本”的方式是自然资本核算体系。根据这一思路,GDP将被纳入“国民幸福”内容,并减去自然资源损耗。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可能会面临“国民不幸福”的困扰,并将从GDP中减去“自然资源消耗”。
GDP背后蕴含的是经济运行体系、治理方式和发展理念,GDP的修正意味着规则的修正。中国的GDP总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二,但还是以“打工”收入为主,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没有本质上升。中国人民是勤劳的,但勤劳只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条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表象背后的规则,并逐步影响、制定规则,才能真正实现复兴。
三、知识产权是规则博弈的核心环节
在全球产业格局重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虽然转出了,但是他们对于最终产品的消费却不降反增,西方跨国公司的利润也是不断上升。可以简单地说这是一种“不劳而获”。这种“不劳而获”的基础,源于国际知识产权体系的实质安排就是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果变相地无偿输送到发达国家。
“知识产权”(IualProperty)一词就其语义来说,经常有两种不同所指:一是指一种法律权利,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等,也包括商业秘密权、公开权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权;二是指上述权利的保护对象,例如可授予专利的技术、可受到保护的商标以及可以保护版权的作品等。为了区别于第二种语义,第一种语义下的知识产权常写作“iualprhts”。实际上第二种语义只是第一种的引申,且并不严格。只不过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知识产权”作为法律权利与作为保护对象是具有相同的利益主体的,因此事实上不需要严格区分,才有了这种语义引申。
以专利权为例,作为保护对象,一般而言他指的是某种技术;作为法律权利,他指的其实是权利人对该技术所产生利益的垄断获利权。显然,与运用技术进行生产从而获利的过程有关的利益主体包括技术研发者、专利拥有者、技术使用者等。过去,专利权人往往与技术研发者和技术使用者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创造知识的主体拥有其相应权利——实际上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创立的初衷也是为了激发人们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这本身就含有“创造者与获益者一致”的假定。
然而随着近年来国际产业大转移的发生,全球产业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重组,技术研发者、专利拥有者与技术使用者之间也出现了分离及转移,使得知识产权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含义。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些过去属于“工业落后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变成了“世界工厂”,是工业技术的主要使用者。而发达国家则随着产业转出,出现了“去工业化”——工业生产越来越少,不再是工业技术的主要使用者,然而发达国家仍然是知识产权的主要拥有者。实际上随着研发过程进入“开放式创新”时代,通过研究外包进行的跨国研发已经成为大多数跨国公司进行技术研发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拥有世界上最多专利权的那些跨国公司,自己并非技术研发者,也不是技术使用者,而只是采购者,但其却拥有专利权,从而获得了经由技术而产生的大部分利润。
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各国纷纷高筑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已取代关税壁垒成为西方国家贸易壁垒的主要形式,以图在日益失去技术优势的情况下维护通过知识产权获利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之间通过日趋复杂化的“交叉授权”形成了庞大的共享“专利池”(patentspool),从专利池中又塑造出许多不断升级的标准体系,对标准本身又进行了专利化,以“无形”的知识产权链条控制了“有形”的全球化研发、生产和销售过程。在WTreementoedAspetellectualPrht,《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协议(草案)》简称)框架下,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会随着保护对象的位移而扩张,可以随着“嵌入”到产品中的零部件而自动把权利“嵌入”到使用国,于是拥有较大“知识产权集群”的国家,实际上可以通过修改国内法律法规来达到影响别的国家利益格局的目的。由此,当代条件下发生的“国内法国际化”博弈日趋激烈。应对这种博弈需要培养大量深刻熟悉工业过程的法律人才。
四、专利权的特许垄断性质
专利权的设置参照对象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特权(privilege),而知识产权的其他项目如商标权、外观图案设计权、著作权、种苗权等则是参照专利权而设置。
一般认为现代专利制度起源于1624年英国议会颁布的《垄断条例》(TheStatuteofMonopolies),该条例宣布废止一切垄断许可,但仅把发明者对自己的发明在一定时期内的垄断作为例外保留下来。《垄断条例》产生的背景是:当时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信奉“君权神授”并且不了解英国国会,滥发了大量独占垄断权许可。由于国王与国会矛盾激化,国会颁布《垄断条例》废止了詹姆斯一世滥发的独占垄断权。詹姆斯一世所颁发的独占垄断权本身就是参照封建领主对领地的特权,专利权作为这些独占垄断权的一种也不例外。因此可以说专利权所保护的利益,实际上参照的是封建地租。日本著名知识产权专家富田彻男指出:授予发明者的专利权与中世纪的特权相比,仅仅稍有差异而已。
五、国际专利制度的基础是市场相互准入
参照封建领地特权而设置的专利权起初是一种国内权利,别的国家是不予承认的。19世纪中期之前,不仅仅是各国在法律上不承认别国专利权,甚至学术理论上也是反对专利权的。当时新兴的自由贸易论把专利权作为垄断之一种而激烈反对,并促使英国国会于1851—1852年进行了关于是否有必要继续实行专利制度的调查,并于1852年制定了专利审查制度。
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各国的经济面貌,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专利法规。互不承认专利意味着可以在别国进行任意仿造或者抢注,实际上当时不少是在鼓励这类做法的。不过随着工业品国际贸易的发展,相互承认专利权其实是必然趋势。
知识产权的跨国保护经历了一个从双边条约到多边条约的历程。以双边条约形式保护知识产权手续烦琐、内容庞杂、效力不一,于是有关国家便寻求通过多边公约形式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ParisfortheProteofIndustrialProperty,简称《巴黎公约》)是第一个多边知识产权保护框架。
《巴黎公约》的产生源于一次国际博览会主办方的尴尬。1873年,在维也纳举办万国发明博览会时,主办方发现很多发明者顾虑展品可能遭到仿制而不愿参展,于是召集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专利改革”的会议。会议提出了若干专利保护原则,并倡议“早日达成专利国际保护协约”。
作为维也纳会议的后续,1878年有关国家又为巴黎世博会召开了国际专利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1883年3月20日,法国、比利时、巴西、萨尔瓦多、意大利、塞尔维亚等11个与会国通过并签署了《巴黎公约》,1884年7月7日开始生效。目前已有174个国家加入了《巴黎公约》。
《巴黎公约》确立的主要原则包括国民待遇原则、优先权原则、专利与商标的独立原则等,从这些原则可以看出,国际专利制度的默认前提是市场的相互准入,只有相互开放产品的市场准入才需要设计这些原则。
在相互开放市场准入的条件下,保护外国人的专利权实际上是保护其获利权,这里的交换是:对方国家也要保护我国公民的专利权。由此不难推论:如果两个国家之间拥有的专利数量相差悬殊,则拥有专利权更多的一方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因而,实际上国际专利体系存在有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性质。200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表的《让全球贸易为全人类服务》报告指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符合发达国家利益,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适合,应予修改。
六、全球产业重组造成国际知识产权的权利—义务不对应
理论上,专利权的保护对象是发明者从技术发明中获得利润的权利,权利来源应该是发明人进行的发明创造劳动。然而现在世界上那些从专利权以及各项知识产权中获得了最多利益的国家,却并不是相应的创造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全球知识创造劳动的分布与知识产权权利分布发生了严重的不对应,并且这种不对应在日益扩大。
过去,知识和技术的完整生产链条大多在一个国家内完成,然而随着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专业转移,知识和技术的生产链条也延伸为跨国长链,在管理学上这就是所谓“温特制”(Wintelism)。
“福特制”生产过程的特点是以分工和效率为基础,强调企业的内部生产过程,形成的是大而全、强而有力的单一生产体系。“福特制”的企业尽管也可能把生产链条进行跨国分布,但还是强调在企业内完成,企业对生产的管控方式主要是最终产品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垂直管理。
“温特制”与“福特制”的根本不同在于完全打破了围绕最终产品进行生产资源垂直安排的模式,改为围绕着产品标准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形成标准控制下的产品模块生产与组合。这一生产架构中,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掌握在极少数国家手中,而大多数生产者则以模块生产的形式,实现和落实着这些标准。在这个架构中,标准和游戏规则取代了最终产品成为生产管理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