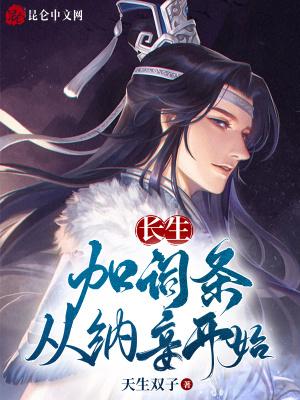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百年变局 > 第三编 数字之变(第2页)
第三编 数字之变(第2页)
从图11-2看,大部分公司2017年下半年人为干预自动驾驶的频率明显下降。Waymo公司1—6月无人驾驶平均英里数是4847英里,7—11月增长了55%。通用公司的无人驾驶里程数也从1—6月的627英里增加到了7—11月的2750英里,增长338。6%。百度也表现不俗,增长了600%,无人干预自动驾驶平均距离达到了119英里。根据加州DMV的数据,当前获准在公路上进行无人驾驶的汽车数量约400余辆(可查数据是409辆)。其中Cruise公司最多,占104辆;其次是苹果和Waymo,分别是55辆和51辆。Waymo公司是当前加州唯一在不配置备用驾驶员的情况下准许在公路进行自动驾驶测试的公司。
但民众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对无人驾驶的担忧却开始越来越强烈。从2018年年初的民意调查看。亚非拉人民对自动驾驶的热情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根据盖洛普2018年年初对1503名美国民众对无人驾驶相关问题进行的调查,有34%的人表示他们期望未来6至10年内美国能普及无人驾驶。有19%的受访人认为未来五年内无人驾驶就会随处可见。
图11-22017年1—11月加州路测汽车自动驾驶的平均英里数(自动行驶距离人为干预次数)
资料来源:V。
民众对自动驾驶的接受程度,各地区差异较大。根据跨国咨询公司益普索集团(Ipsos)近期对中、印等15个国家2。15万人的抽样调查表明,亚非拉国家普遍比较欢迎自动驾驶,而西方发达国家反对人数占比反而更多。如图11-3所示,印度和中国对自动驾驶最热情,分别有49%和46%的人表示非常期待。根据Ipsos的调查,在南美,巴西有31%受访者表示欢迎自动驾驶,和俄罗斯接近。但美国可能由于受最近几个月无人驾驶车祸事件的影响,有近四分之一的人表示不会尝试自动驾驶。欧洲国家反对自动驾驶的人也比较多,德国占31%、法国和英国分别占25%和24%。加拿大也有24%的人表示明确反对。
虽然无人驾驶汽车发展过程引发了民众对于安全的焦虑,但究竟是进一步加强监管还是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当前从美国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因为存在风险而加强对无人驾驶的束缚。
图11-3部分国家民众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态度(省略态度中立人数占比)
资料来源:Ipsos。
根据皮尤调查2016年的数据,2006—2016年十年中,美国的人类驾驶员造成4万人不必要的死亡。换句话说,每天有100人被一名人类驾驶员杀死。另一方面,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将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低多达90%。[4]这意味着延迟的成本由于监管焦虑而无人驾驶的汽车技术每年将导致成千上万的不必要的死亡。莫卡特斯中心(Merter)模型表明,5%的监管延迟可能会产生额外的15500例不必要的死亡事故。延迟25%意味着112400名不必要的死亡。[5]所以,从长远发展看,因为害怕无人驾驶带来的风险而限制其发展,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因为无人驾驶较之于人类驾驶,有着显然的优势。其他人工智能领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3。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发展遇到的问题
一是大数据生态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前人工智能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需要依托大数据对机器智能进行训练。在这一方面,目前我国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大数据生态系统方面落后于美国,缺少统一的标准和跨平台的共享。二是公共大数据开放依然有限。开放政府大数据有助于私营部门的创新,但我国的公共部门开放的大数据依然相对少。三是跨国大数据流动的安全问题,我国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二是人工智能人才问题。我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方面依然落后于美国,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人才依然短缺。当前我国对高端人工智能人才的渴求依然是非常强烈的。美国超过半数的资据科学家拥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但据麦肯锡统计,我国相关领域经验不足5年的研究人员高达40%。我国当前只有不到30个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大学研究实验室,仅靠这些实验室是无法产出足够的人才来满足人工智能行业的需求的。此外,我国当前人工智能人才分布也不均匀,主要集中在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领域,而其他领域的人才相对更少。
三是人工智能核心硬件依然存在诸多不足。我国的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s)长期以来严重依赖进口,部分类型的高阶半导体则几乎完全依靠进口。为解决这一难题并掌握半导体核心技术以提高我国在未来更广泛地部署人工智能领域的能力,我国在2014年发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和《中国制造2025》,并设立了一个超过200亿美元的基金,通过并购、投资入股国内外半导体产业等,积极扶持国内半导体产业,虽然已见初步成效,但自主创新之路仍然艰辛漫长。
4。对未来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建议:夯实基础,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
纵观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有低谷,也有高峰,一路走来,在曲折中前进。回顾历史,人工智能的发展既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受到市场利益的推动。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越来越广泛,它会促进全行业数据的加速产生,推动移动化计算的发展。在垂直领域,AI也会向商业化发展靠拢,创造出更多的直接经济价值。因此,回归基础建设,完善大数据生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然是当前我国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重点,这三项基础工作做好了,才能进一步激发社会的创新能力,激活企业的人工智能创新动力,为我国在数字时代的腾飞培育坚实的核心动能。
三、机器与人的融合与抗争
截至当前,类人机器人走进人们的生活依然还需要时间。但是工业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已经对制造业竞争力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根据牛津经济研究所2019年6月公布的《机器人如何改变世界》的报告,每3个新的工业机器人中,就有一个是在中国上线。牛津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平均每新安装一个机器人,就会取代1。6名制造工人。到2030年,预计全球有大概2000万个制造业岗位将会被取代。牛津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同时表明,机器人化的负面影响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低收入地区的影响会更强。新增长的机器人在低收入地区取代的工作岗位几乎是同类高收入地区的两倍。[6]
1。机器人的发展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更大
机器人的兴起对世界各地的工业就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11-4表明每增加一个机器人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要明显小于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机器人会带来财富,但并不一定能带来共同富裕。
图11-4机器人增加对就业的影响
资料来源:OxfordEics。
随着机器人应用的不断增加,将会产生一种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机器人的应用能带来增长;另一方面却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智能化将会不断推进全球的区域不均和两极化。根据牛津经济研究所对3。5万名美国人在其职业生涯中的工作变动情况进行的分析表明,在过去二十年中,超过一半的离职产业工人被吸收到三个职业类别:交通运输、建筑和办公室类工作。但牛津经济研究所的分析发现,这三个职业领域是未来十年最易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领域。然而,这些发现不应该导致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试图阻碍机器人技术的采用。相反,挑战应该是通过帮助弱势工人做好准备并适应其带来的剧变,更均匀地分配机器人股息。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技术公司、教育工作者和工人都可以发挥作用,这需要政府和社会的系统调节。
2。机器将不仅仅是提高工人工作效率的工具,机器本身变成了工人
20世纪6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访问某个国家时发现该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项目中有大量的人在使用铲子挖土,而很少用推土机、拖拉机或者其他重型土方设备。弗里德曼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当地政府官员解释说这样是为了增加就业。弗里德曼反问当地官员:“如果是为了增加就业,为什么用铲子而不是用勺子让他们挖土?”
经济学家们经常引用弗里德曼的这个反问来反驳对机器破坏就业和造成失业的可能性的担忧。回顾历史,也证明这种反驳是有很强的历史依据的。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推动着人类走向更加繁荣的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蒸发了数百万人的工作机会,驱使大量失业的农民进入城市寻找工厂工作。后来,自动化和全球化推动工人走出制造业并进入新的服务领域工作。在这些产业转型和技术交替的过程中,人们自身的调整、短期失业往往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不可否认,技术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但同时会剥夺工人之前的机会,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应对改变,并进行高适应性的调整。
从积极的方面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五年里,科技的发展成就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生产中使用机器的改进,操作这些机器的工人的生产率也同样增加,使它们更有价值,并允许它们要求更高的工资。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随着科技发展带来良性反馈循环推动美国经济向前发展,也成就了西方经济学的辉煌。正是在同一时期,西方经济学开始逐步成为一种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科学。西方经济学开始逐渐转向由复杂的定量和统计技术所主导的学科。西方经济学家们开始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这种长期的繁荣,让这个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并认为西方经济的逻辑是自然规律并且永远有效。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往的西方经济学是面临着挑战的。因为人类的生产关系的基本假设正在改变。历史上,机器是作为提高工人生产能力的工具而存在的。但是,现在机器本身正在变成工人,资本对劳动力的定义也在发生改变。2017年,比尔·盖茨曾公开表示机器人和人类一样应该交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机器与人生产关系变化现象问题的关注。然而,机器人对人的挑战还远不止于此。“写作机器人”“智能人力资源管理”等系统的出现,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作人员所感知到的危机也越来越多。机器越聪明,不仅需要的工人越少,需要的白领也会逐步减少,人与机器的界限会逐渐模糊,未来的变数将会逐步加大。当机器成为工人本身,机器为主体单元的劳动创造价值,未来的变数会加大。
3。马斯克“脑机接口系统”会开启赛博人类时代吗
“赛博人”一词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空飞行试验。当时,美国两位科学家在一只小白鼠身上安装了一种渗透泵,自动把化学物质注射进小白鼠,以控制它的生化反应。他们在发表的论文中,给这只小白鼠造了一个新词叫“赛博格”(cyb),是由“控制论的”(etic)与“有机生物体”(anism)两个词语拼贴而成,意思是“自动调整的人类机器系统”。1985年,哈拉维提出著名的赛博格宣言,她将赛博格定义为“无机物机器与生物体的结合体”。比如,装了假牙、假肢、心脏起搏器等的身体,都可以被当做“赛博格”。这些身体模糊了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简言之,就是人机结合的人,简称为赛博人。
由埃隆·马斯克(ElonMusk)所创办的Neuralink开发的脑机接口首先采用了柔性“线程”连接模式,减少了对大脑的损伤。在2019年7月的发布会上,马斯克发布了一项最新的成果,一只猴子能用大脑控制电脑。图11-5是嵌入到老鼠内的Neuralink系统,还提供了USB-C接口。未来的人脑读取和存储信息,会不会像U盘拷贝一样迅速呢?如果按马斯克团队所探索的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