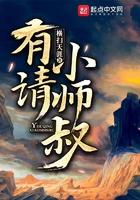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同频痛觉 > 叩门(第2页)
叩门(第2页)
“回来啦?洗手,准备吃饭。”父亲抬头看了她们一眼,额头上带着忙碌后的细密汗珠,语气是一贯的、带着些许不易察觉的疲惫的温和。
母亲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低头整理着一叠似乎是单位带回来的文件,听到动静,抬起头,目光习惯性地、如同最精密的扫描仪一般,在阮笙的脸上快速而仔细地掠过,像是在进行每日雷打不动的例行检查与评估,不放过任何一丝可能泄露内心波动的细微表情。
餐桌上,气氛是这个家庭惯常的、带着一丝微妙距离感和无形规则的安静。只有阮曦,仿佛自带屏蔽功能,依旧挥舞着小勺子,声音清脆悦耳,锲而不舍地继续着她的“今日新闻续集”,试图将快乐分享给每一个家庭成员。
阮笙小口吃着碗里粒粒分明的米饭,味同嚼蜡,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寻找一个最合适、最不突兀的时机开口。心脏在胸腔里小心翼翼地、如履薄冰地跳动着,像一只高度警惕的、准备随时缩回坚硬外壳里的脆弱蜗牛。
终于,在父亲起身,准备去厨房为每人盛一碗温热的紫菜蛋花汤的短暂间隙,她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周遭所有可用的勇气都汲取过来。她抬起眼,目光先是落在正在低头喝汤的母亲身上,然后微微转向父亲的方向,声音被她努力压制着,维持着一种尽可能的平稳,但尾音处,依旧泄露了一丝几不可查的颤抖:
“妈,爸,”她顿了顿,清晰地感受到父母的目光如同两盏骤然调亮焦距的探照灯,同时精准地聚焦在自己脸上,喉咙一阵发紧,干涩得厉害,“晚上……林净她们,就是上次……一起去陶艺馆的那几个同学,会过来一趟。”
母亲的眉头几不可查地蹙了一下,形成一个浅浅的“川”字,手中盛汤的动作微微一顿:“哦?来家里?这次是做什么?”那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和潜藏的、源于上次“火锅店事件”的忧虑与不信任。上一次她们带着阮笙和阮曦“先斩后奏”的出逃经历,显然在这个家庭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投下了一颗石子,留下了圈圈扩散的、警惕的涟漪。
阮笙强迫自己迎上母亲那带着探究意味的目光,不让自己的视线有丝毫闪躲,将早已在心底排练过无数次、也是最真实无懈可击的理由,清晰而缓慢地吐出:“我们手工课小组作业的笔筒,就是上次我们一起做的那个,今天烧制好了,她们晚自习后正好顺路去取,说……帮我送过来。”她刻意在“小组作业”和“顺路”上加了不易察觉的重音,强调其正当性与偶然性。紧接着,她的话锋极其自然地、如同行云流水般一转,视线温柔地落向正眨巴着大眼睛、好奇地听着大人对话的小妹,语气放得更软了些,“而且,曦曦之前不是一直念叨,想再让姐姐们看看她房间里收集的那些‘宝贝’吗?彩色石头和亮晶晶的贴纸什么的。”
理由充分,逻辑完整,并且巧妙地、不着痕迹地拉入了阮曦作为情感上的“人质”和事实上的“共犯”。这一招,几乎是百试百灵。
果然,阮曦立刻像是被按下了某个开关,用力地、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小脸上写满了毫无伪饰的期待与兴奋,声音清脆地附和:“嗯!嗯!我的彩虹贝壳和会发光的玻璃珠要给净姐姐看!也要介绍给沐姐姐和鱼姐姐认识!”
父亲的脸上露出一丝恍然,随即是“原来如此”的、放下心来的轻松,他向来不太过多干涉女儿们这种看似正常、健康的同学交往,只要不耽误学习、不出格就好。母亲那带着审视与权衡的目光,则在阮笙努力维持平静的脸上和阮曦那雀跃得快要坐不住的小脸上,来回扫视、评估了好几秒,像是在心中默默计算着这次突如其来的“社交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与它所具备的合理性之间的比值。最终,那细微的、带着怀疑的审视慢慢褪去,融化在女儿清澈的眼神和孙女纯粹的快乐里,化作一种略带无奈的、程式化的、带着明确边界感的叮嘱:
“……行吧。”母亲终于松口,声音恢复了平时的语调,但目光却意有所指地、警告性地瞥了一眼紧挨着客厅的、房门紧闭的书房方向,“让她们别太晚,九点前必须结束。也别闹出太大动静,说话声音都小着点,你外公晚上需要绝对安静。”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像是最终拍板定论,“来了就直接去你房间,别在客厅逗留太久。”
“嗯,我知道。谢谢妈。”阮笙垂下眼睫,浓密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在过于苍白的脸颊上投下淡淡的阴影,她轻声应道,心里那根一直紧绷到几乎要断裂的弦,终于得以稍稍松弛了一些,一股混合着疲惫与成功的虚脱感悄然蔓延开来。
第一步,叩开家庭内部的这扇门,成功了。
夜幕如同巨大的天鹅绒幕布,缓缓降落,彻底笼罩了白日喧嚣的城市。晚自习结束的铃声,如同一声嘹亮而清晰的号角,划破了校园夜晚的沉寂,在各个教学楼之间激荡、回响。
林净几乎是铃声落下的第一个瞬间,就像一颗出膛的子弹,从自己的座位上弹射而起,一把抓起早已收拾好的书包,精准地左右开弓,分别拉住还在不紧不慢扣上笔帽的沐羚和刚刚合上书本的郁纾,语气急促得像是身后有追兵:“快!速度!陶艺馆!争取在人家关门前最后一秒冲进去!”
三人组成了夜晚校园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几乎是踩着铃声的余韵,小跑着穿过了被路灯勾勒出朦胧轮廓的操场、寂静的林荫道。林净一边跑,一边还不忘从校服口袋里掏出那张被她反复摩挲、已经带着体温和些许潮气的便签,就着路边昏黄而温暖的光线,飞快地再次确认上面的字迹:“XX路XX小区X栋X单元XXX室……没错!都记牢了吗?千万别走错了!这可是神圣的使命!”
沐羚的气息依旧平稳,即使在奔跑中,她的声音也保持着固有的冷静和条理,大脑飞速运转着:“根据城市地图比例尺与步行速度常规值进行测算,从陶艺馆所在地点到目标地址,最优路径步行约需十五至十八分钟。考虑到我们所携带物品的易碎属性与非规则形状,需适当控制步速,避免剧烈颠簸,预计总耗时在二十分钟内。”
郁纾沉默地跟在她们身侧,夜晚微凉的风调皮地拂起她额前几缕墨色的碎发,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和那双在夜色中显得更加深邃沉静的眉眼。她没有参与旁边两人关于路线和时间的讨论,薄唇紧抿,但步伐却异常坚定,方向明确无误,仿佛体内自带精准的导航系统。
所幸,陶艺馆那扇挂着风铃的玻璃门后,灯光还温暖地亮着,像黑夜中一座小小的、等待她们的灯塔。年轻的、扎着丸子头的老师看到这三个跑得脸颊微红、气息不匀的女生,了然地笑了笑,转身从后面的陈列架上,将那个已经完全冷却、仿佛沉睡了许久的“友谊之树”笔筒取了出来,递到她们面前。烧制后的笔筒,釉色沉静内敛,白色的底釉温润如玉,上面雕刻的线条——阮笙那条蜿蜒曲折的河流,郁纾那些层叠起伏的山峦,林净那盘根错节、充满野性生命力的树根,沐羚那笔直挺拔、充满支撑感的树干——所有的一切都在高温下完美地融合、固化,形成了一个微缩的、坚固的、只属于她们四人的小小世界。
林净小心翼翼地、如同对待初生婴儿般,用早已准备好的、柔软的棉布将它细细包裹好,然后郑重其事地、双臂稳稳地环抱在胸前,仿佛怀抱着一件足以改变世界的、稀世的珍宝。
“好!全体都有!”她深吸了一口夜晚清冷的空气,眼神里闪烁着使命必达的、近乎虔诚的坚定光芒,“目标,笙笙的城堡!出发!”
夜晚的街道比白日里安静了许多,白天的车水马龙变成了偶尔驶过的车辆,路灯尽职地将昏黄的光线倾泻下来,将她们三人并排前行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又随着脚步的移动缓缓缩短。林净抱着笔筒,走在最前面,脚步轻快中带着谨慎;沐羚在一旁,不时观察着道路两旁的店铺招牌和路口指示牌,像最严谨的领航员,确保着行进路线的绝对准确性;郁纾依旧保持着她的沉默,但她的目光偶尔会掠过林净怀中那个被软布包裹的、隆起的形状,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又或者会抬起眼,望向远处那片密度极高的、闪烁着万家灯火的居民楼,深邃的眼底映照着点点星光,无人知晓那平静的表面下,究竟在思考着什么。
越靠近阮笙家所在的那个略显老旧却充满生活气息的小区,一种无形的、混合着强烈期待与微妙紧张的气氛,开始在三人心照不宣的沉默中悄然弥漫、发酵。她们即将踏入的,不仅仅是XX路XX小区X栋X单元XXX室这个物理空间,更是阮笙从未向外人展示过的、剥离了所有学校伪装后的、最真实也最脆弱的生活现场,是她所有情绪和秘密的存放地。
“根据门牌号排列规律,就是前面那栋,靠里的那个单元。”沐羚指着不远处一栋外墙有些斑驳、阳台晾晒着各色衣物的六层居民楼,冷静地宣布。
林净在单元门口停下脚步,下意识地空出一只手,整理了一下自己并不凌乱的校服衣领和额前被风吹乱的碎发,又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登台前最后调整自己的状态。她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沐羚和郁纾,三个人的眼神在昏暗的光线下短暂交汇,空气中流淌着一种无需言语的、坚实的默契与相互支撑的力量。
她们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物品送达任务。
这是一次郑重的拜访,一次温柔的“叩门”。
她们即将用自己的方式,在阮笙那片寂静荒芜的领地上,共同栽下一棵名为“友谊”的树,并期待着它,能够生根,发芽,最终枝繁叶茂。
三人并肩,踏上了通往那个特定楼层的、略显狭窄的楼梯。夜晚静谧的楼道里,回荡着她们清晰而坚定的脚步声,一声声,敲响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