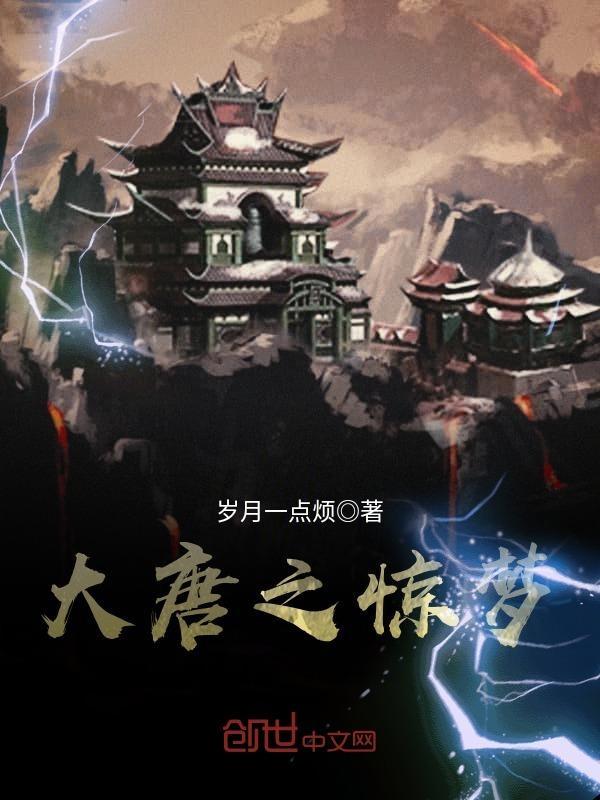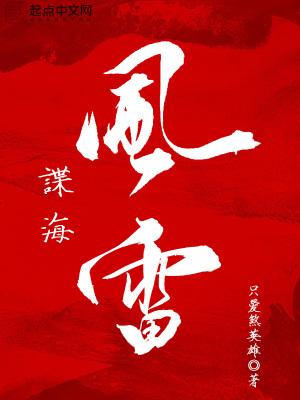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戍光志愿雄赳赳 > 第十五章策略与交锋(第1页)
第十五章策略与交锋(第1页)
第十五章策略与交锋
嘉梁的晨光穿透云层时,马向东家的堂屋已亮起了第三盏煤油灯。
八仙桌上摊开的,是一份铺满整张桌面的《嘉梁后山生态文化保护专项报告》。左侧是索娜团队的地质监测数据,红色曲线标注着滑坡预警的临界值;中间是周明远翻出的古籍抄本与文物普查图,泛黄的宣纸上用朱笔圈出羌人古墓群的四至边界;右侧是马向东手绘的补充标注,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着“此处有暗沟,民国三十年山洪冲毁过古道”“这棵老松是水脉标志,根下三米即泉眼”——三代人的智慧、三种领域的专业,在这份报告里完成了最紧密的咬合。
“这里的数据有出入。”马远指着屏幕上的地质剖面图,眉头紧锁,“索娜姐的监测显示此处是坚硬岩层,但爷爷的地图标注是‘流沙层’,我们实地探查时也确实发现了流沙痕迹。”
索娜凑近屏幕,指尖划过数据曲线,眼神凝重:“可能是监测设备的探测深度不够。流沙层藏在岩层下方,常规设备很难发现。”
马向东拿起拐杖,轻轻敲了敲桌面的地图:“没错,这是‘假岩层’。当年剿匪时,我们在这一带设伏,土匪踩塌了流沙层,掉下去三个,再也没上来。”他伸出手指,在地图上画出一条隐蔽的弧线,“流沙层下面连通着地下水脉,一旦施工挖穿岩层,流沙会瞬间堵塞水脉,山下的泉眼都会干涸。”
索娜立刻打开电脑,调出三维地质模型,按照马向东的描述修正参数。当新的模型生成时,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原计划的索道桩基位置,恰好落在流沙层与岩层的交界处,施工时不仅会触发流沙坍塌,还会直接扰动下方的水脉通道,引发的连锁反应比之前预测的更严重。
“必须把这个补充进去!”马建国拿起笔,在报告上重重圈出这处风险点,“这是老兵们用命换来的经验,比任何设备都准。”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堂屋的灯光从未熄灭。马建国负责整合所有资料,用老兵的朴实语言将专业数据转化为易懂的表述;马援朝联系消防系统的技术专家,对地质灾害风险进行二次评估,补充了救援难度分析;马远将报告做成图文并茂的PPT,同步上传到网络平台,标注“嘉梁全体居民联名请愿”;索娜和周明远则带着报告样本,奔赴省城,直接对接省自然资源厅和文物局的相关科室。
报告的最后一页,是“戌光志愿者”全体成员的签名,三十个名字歪歪扭扭却力透纸背,最下方是马向东用颤抖的手写下的八个字:“一寸山河,一寸守护”。
与此同时,一场别开生面的“行走的抗议”正在策划中。
“我们不能只在会议室里争辩,要让人们亲眼看到后山的价值。”□□在志愿者协会的院子里,对着三十位老兵和二十多位自发加入的市民说道,“古道是活的历史,山水是生的根基,只有亲身走一走,才能明白为什么不能开发。”
行走路线被精心设计:从古城西门出发,沿茶马古道遗址上山,途经羌人石刻群、千年古松、三眼泉眼,最终抵达古墓群外围的观景台,全程五公里,每一处都藏着嘉梁的密码。
出发那天,天朗气清。马向东出人意料地走在队伍最前面,依旧穿着那件藏青色中山装,胸前的军功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的步伐比平时更慢,后背的旧伤让他每走一步都要微微皱眉,却拒绝了马建国的搀扶:“守护的路,得自己走。”
队伍里既有白发苍苍的藏族老人,也有背着相机的年轻游客;有之前支持开发的商户,也有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马远和索娜走在队伍中间,轮流讲解:“大家看路边这些刻着纹路的石头,这是羌人的‘路引石’,当年马帮就是靠着这些纹路辨认方向……”“这棵千年古松,根系覆盖范围达五十米,是后山水土保持的核心,它的存在能减少30%的滑坡风险……”
走到三眼泉眼处,泉水清澈见底,冒着氤氲的水汽。马向东停下脚步,转身面对队伍,声音沙哑却清晰:“这三眼泉,分别叫‘生泉’‘养泉’‘灵泉’。生泉供人饮用,养泉灌溉农田,灵泉滋养草木。当年大旱三年,山下所有水井都干了,就这三眼泉没断过水,救了整个古城的人。”他蹲下身,用手掬起一捧泉水,“这水不是普通的水,是嘉梁的血脉,挖断了山,就断了血脉。”
一位之前强烈支持开发的汉族商户,看着泉眼旁刻着的“道光年间重修”字样,又看了看马向东苍老却坚定的眼神,眼眶红了:“马老班长,我之前糊涂,只想着赚钱,忘了祖宗留下的东西才是最金贵的。”他转身对身边的同伴说,“这开发项目,我坚决反对!谁要是敢毁了泉眼,我第一个不答应!”
队伍走到羌人石刻群时,周明远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拓片,与岩石上的纹路比对:“这些石刻距今已有两千多年,记录的是羌人祭祀山神、祈求风调雨顺的场景。每一道纹路都藏着古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他们知道后山脆弱,所以只敢在岩石上刻字,从不敢轻易动土。”
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拍摄石刻和泉眼,将所见所闻发到社交平台。#嘉梁古道的千年密码##老兵守护的不只是山#等话题很快登上本地热搜,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关注这场“不吵架的抗议”,甚至有外地的文物保护者和环保人士表示要赶来支援。
然而,旅游公司的动作比他们预想的更快。
就在“行走的抗议”进行到第三天时,马援朝收到消息:旅游公司绕过社区和志愿者,以“紧急地质勘探”为由,连夜调来了三支工程队,带着挖掘机、钻机等设备,准备清晨时分强行进入后山施工。
“不好!”马援朝立刻拨通了马建国和□□的电话,“工程队已经到山脚下了,估计半小时后就会进山!”
马建国正在给新加入的志愿者讲解古道历史,接到电话后脸色大变:“所有人立刻赶往西山口!阻止他们进山!”
队伍立刻掉头,朝着西山口狂奔。马向东的脚步踉跄,却依旧咬牙坚持,马远想背着他,被他一把推开:“我能走,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西山口,是后山唯一的入口,狭窄的山道旁是陡峭的悬崖,是守护后山的最后一道屏障。当马建国带着队伍赶到时,三支工程队已经集结完毕,十几辆工程车一字排开,挖掘机的铁臂高高举起,蓄势待发。
旅游公司的副总站在最前面,穿着西装,脸上带着倨傲的笑容:“马建国,识相的就让开!我们有合法的勘探手续,你们再阻拦,就是妨碍公务,别怪我们报警!”
“合法手续?”□□上前一步,举起手里的《专项报告》,“你们的手续是在隐瞒地质风险、伪造文物评估的情况下拿到的,根本不合法!这是我们提交给省厅的报告,上面明确指出,后山不能进行任何大规模施工!”
“报告?不过是你们自己编造的谎言!”副总不屑地笑了,“我告诉你们,今天这勘探,我们做定了!谁也拦不住!”他对工程队领队使了个眼色,“开工!谁敢阻拦,直接报警!”
挖掘机的引擎轰鸣起来,铁臂开始转动,朝着山道入口挖去。
“住手!”马向东突然大喊一声,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穿透人心的力量。他走到队伍最前面,缓缓坐下,后背靠着山道旁的岩石,拐杖横放在身前,像一座不可逾越的界碑。
“马老班长!”三十位戌光志愿者立刻跟着坐下,整齐地排列在马向东身后,形成一道人墙。他们虽然年迈,有的甚至需要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却个个眼神坚定,挺直了腰背。
“还有我们!”之前支持开发的汉族商户大喊一声,带着十几位市民也坐了下来,“要挖山,先从我们身上碾过去!”
“不能让他们毁了家园!”越来越多的市民围了过来,有藏族阿妈,有汉族老人,有年轻的学生,他们自发地加入静坐的队伍,人墙越来越厚,将工程车牢牢挡在外面。
副总脸色大变:“你们……你们这是妨碍公务!我现在就报警!”他掏出手机,就要拨号。
“你报吧!”马远上前一步,打开手机直播,“我们现在就在直播,让所有人看看,旅游公司是怎么在隐瞒风险、伪造手续的情况下,强行破坏文物和生态的!”
直播间的人数瞬间飙升,弹幕刷屏:“支持老兵!守护家园!”“旅游公司太无耻了!”“严查背后的利益链条!”
副总看着马远的手机,手微微颤抖,最终还是放下了手机。他知道,一旦报警,事情闹大,他们伪造手续的事情很可能会曝光,到时候不仅项目泡汤,自己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给我上!把他们拉开!”副总急了,对工程队的工人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