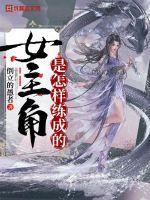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历史与现状(上下册) > 哲学主题导引(第1页)
哲学主题导引(第1页)
哲学主题导引
[英]格雷林江怡编译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序言:西方哲学的主题及其领域[1]
一、作为探究和反思的哲学
哲学探究的目的旨在获得对知识、真理、理性、实在、意义、心灵、价值等问题的洞见。其他人类活动探索(不仅是指文学艺术),是针对这些相同问题的不同方面,但只有哲学才是直接拷问它们,希望能够澄清这些问题,并尽可能地回答这些问题。
“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字面意思是指“爱智慧”。但更为准确的定义则应当是“探究”或“探究与反思”,这些词表达了最为宽广的范围,是指关于世界以及其中的人类经验的最一般特征的思想。在最初的年代,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等学问当时还没有区分开来,哲学就是对万事万物的研究。在这种意义上可以确信,古希腊人开创了西方哲学,因为他们自由地探索世界和人类的一切方面,这并非始于宗教或迷信原则,而是始于相信人类理性有能力对有兴趣的一切事物或对人性有意义的事情,自己提出正确的问题,并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希腊人思索着物理宇宙的起源、构成和功能。他们讨论着人类的伦理和政治环境,提出关于最佳配置的观点。他们研究人类理性自身以及真理和知识的性质。他们由此就触及到了几乎所有主要的哲学问题,并由此带来了巨大的思想遗产。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大致是从14世纪到17世纪),西方思想受到了基督教的支配。这并非是说当时没有哲学,完全不是那样;但当时的大部分哲学都是服务于神学的,或至少是(除了在逻辑学的情形之外)受到了神学思想的限制。17世纪涌现出的许多复杂事件,出于便利而被标记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些事件持续了两个世纪,这时出现了哲学探究的强有力的复兴。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相关,开始询问关于知识性质的根本重要的问题。这种思想自由也推进了道德和政治问题之争的复兴。
根据近代思想史的某些观点,我们可以把哲学看作是诞生了17世纪的自然科学、18世纪的心理学、19世纪的社会学和语言学;而到了20世纪,哲学则在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等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毫无疑问,这过分简单化了哲学反思的作用,但却也并非夸张之辞,因为哲学最后的确构成了对一切事物的探究,虽然并非完全被理解为构成了自足的知识分支。一旦确定了正确的问题以及回答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这种探究的领域就成为独立的追求。例如,在所描述的迷信史中,只要对宇宙的物理性质和属性的哲学反思确定以恰当的方式询问和回答问题(在这里主要是以经验的和数学的手段),那么哲学就会停止,这种探究就变成了科学。
哲学由此就保持了这样一种探究,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悖论,这个探究试图通过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使得自己终结,或者是找到能够使自己转变为具体探究的科学如物理学、心理学或历史的方式而使得自己终结。根据“区分和征服”的原则,对哲学的系统研究最终就使得自身成为哲学探究的领域:“伦理学”、“政治哲学”和“逻辑学”多少都是对自身主题的自我解释,而“认识论”(对知识性质的探究)和“形而上学”(对实在终极性质的探究)则需要根据第一层次的更多解释(还有其他对具体主题的哲学探究,比如科学哲学、法律哲学、历史哲学等,哲学家们在其中讨论的都是对这些具体追求的假定、方法、宗旨和主张的反思)。
二、认识论探究知识的性质和获得知识的方式
认识论或知识论是哲学的分支,考察的是关于知识的性质和我们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它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知识?”“什么是获得知识的最为有效的方法?”正如下面的讨论所表明的,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但要回答这些问题却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
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有效方法是要考虑公认的知识定义。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以往争论中,知识标准地被定义为经过证明的真信念(justifiedtruebelief),因为至少看上去最为可能的是,知道某个东西就一定相信它,关于它的信念就一定是真的,而人们相信它的理由从某个标准看来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人们不会去说知道某个东西,是由于他随意地或偶然地决定去相信它。所以,这个定义三个部分的每一个都明显地表达了知识的必要条件。这种主张就是,它们共同满足了知识。但这个观念存在一些难题,特别是需要把真信念说成是知识的证成(justifi)。为了处理这个难题,形成了各种对立的理论。
伴随着如何定义“知识”的争论,另一个涌现出的争论是关于我们如何获得知识。在认识论的历史中,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思想流派(这是为了简便而大致地说):“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前者认为,获取知识的主要路径是训练理性;而后者认为,获取知识的主要路径是知觉(使用观、听、闻、味、触五官,以及借助于工具对它们的扩展,比如望远镜、显微镜等)。理性主义者的模型是数学和逻辑,通过理性的推理就可以得到必然真理。经验主义者的模型则是一切自然科学,观察和实验是其中的主要探究动力。过去几个世纪的科学史强化了经验主义者的观点;但就真正的理性而言,关于知觉的问题却变得更为重要了。
不过,对认识论的这两个传统来说,核心的问题是要研究我们获得知识的手段是否值得信赖。要确定在这种联系中需要强调的问题的明显方式,是要考察怀疑论提出的挑战。
因此,关于知识的性质、获取知识的方式以及面对怀疑论的挑战,这三个讨论共同构成了认识论的主要内容。当然,认识论中还有其他一些争论,比如记忆、判断、沉思、推理、“先天—后天”区分、科学方法等,但掌握了这里的三个核心讨论就构成了理解其他各种争端的基础。
三、哲学逻辑帮助人们有效地表达思想
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富人都很快乐而且约翰是富人,我们就可以推出约翰是快乐的。如果我们知道土豆已经煮了二十分钟,我们就可以推出它们快要煮熟了。
这些例子显然属于不同种类的推论。我们把第一个称作演绎上有效的推论,其标志是,如果我们由此推论的东西是真的,我们所要推出的东西为假,就是不可能的。我们把第二个称作归纳上的强推论,其标志是,尽管我们由此推出的东西对所要推出的东西提供了很好的理由,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理由。在高原地带,水会在较低的温度上沸腾,烹调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即使是在通常的高度,某些土豆也会非常坚硬。
第一种推理要求的是演绎的有效性。有一组问题是与逻辑学家们使用的概念性质相关:真理,逻辑真理,有效性,蕴涵。另一组关心的是分析在推理中很重要的习惯用法的性质,比如条件句。推理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推论。逻辑学家们研究的是使得推理有价值的推理特征:这就是保真性或有效性。典型地说,一段推理就是从一个或更多的(至少是暂时有根据的)陈述推出某个其他的陈述。起点叫做前提,终点叫做结论。由某个前提和结论构成的一套陈述就叫做论证。关于论证的有效性的标准定义是:一个论证是有效的,当且仅当,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对所有的陈述都是不可能的。
对有效性的研究涉及研究推论。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从“拿破仑是有活力的”这个前提到“某个人是有活力的”的论证是有效的吗?就是说,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这是不可能的吗?我们倾向于回答“是的”。在这种情况中,当我们被问到从前提“最大的素数不存在”到结论“某个东西不存在”这个论证,我们难道不应当给出相同的回答吗?我们对在第二种情况中回答“是的”应当会感到一些不安:因为这个前提为真,有效性也保证为真,所以这个回答就会使我们认为某个东西不存在;这看上去轻点说是很奇怪的,重些说则是发疯了。
研究哲学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在于,要去了解如何表达和捍卫你自己的观点。你的观点并非一定要成为前人从未提出的观点。在逻辑上,新的观点很难被接受。只要你相信一个观点并愿意去捍卫它,这个观点就可以算作是你的。
有时,特别是在最初的学习中,人们并不会感到能够决定两种对立的理论中哪个是对的。不过,人们应当能够作出这样一个决定:这个论证决定性地确立了或反驳了这个理论吗?一个反驳是可以为这个理论的变形避免的吗?人们至少无法区分这个那个理论的两种形式吗?只要研究哲学是值得的,询问和回答这些问题就是至关重要的。
方法论的主题最好定义为逻辑主题的对立面。逻辑是对有效演绎推理的研究:在一个有效演绎论证中,前提为结论提供了结论性理由;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实际上从事的大多数推理都没有满足这个理想。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中,我们使用的论证并没有为结论提供结论性的理由。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可能给了我们去相信这些结论的很好的理由,但并不以如同演绎论证那样的绝对方式强迫我们。
对方法论的讨论主要考虑的是这种非结论性推理以及在试图理解这种推理中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1)归纳及其问题;(2)自然法则;(3)实在论、工具主义和未确定性;(4)确证和概率;(5)解释。
四、形而上学是对实在的终极性质的研究
形而上学是一门哲学分支,讨论的是实在的终极性质。它的首要问题是:“何物存在?”也就是说,什么存在着?以及“它像是什么?”“何物存在”这个问题并非要引入回答宇宙间的万物,比如,我的左脚,我的右脚,我的笔,这张纸等等,而是要对实在的基本特征给出一种一般性的描述。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这个事业就是“对存在作为存在的研究”(thestudyofbeingquabeing)。这些主要问题可以很快地引起其他问题。能够谈论何物存在,也就能够谈论存在的性质。某物存在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去理解对存在的断定和否定,比如“夸克存在”或“独角兽不存在”。一旦这些都被看作是对“何物存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例如占据空间和时间的物质对象,上帝或诸神,比如数字、属性和意义这样的抽象实体,那么马上就会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比如,是否只有一个或某个或某些种类的事物真的是终极的?真正终极的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些事物中的某个事物只是出于概念的便捷而存在,那么它是哪一个?如果存在着不止一个事物,特别是如果存在着不止一种事物的时候,那些存在着的事物之间有什么联系?如此等等。
形而上学问题的确数量繁多,意义重大,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构成了哲学自身的分支,例如,心灵哲学和哲学神学。但是关于事物种类的存在和性质的形而上学问题则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哲学争论之中。它们出现在伦理学中,与价值的性质相关;它们出现在数学哲学中,与数学实体(数字和集合)的性质相关;它们出现在认识论中,是因为关于知识性质的问题无法独立于关于知识对象的问题而得到解答。
伴随着更为专门问题的压力,也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域。什么是时间?殊相比事件更为基本吗?人类是否有意志自由?表象与实在之间有区别吗?如果有的话,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什么是因果性?在什么意义上共相是存在的?世界独立于我们关于它的知识而存在吗?什么是实体?等等。我们会不断地看到,对核心和重要的形而上学话题的讨论将成为其他研究的首要基础。这里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因果关系,时间,共相,实体。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大部分的哲学及其历史就变得更为突显了。
五、心灵哲学是对常识心理学性质的辩护
大致地说,心灵哲学是处理心灵问题的哲学领域,其中的许多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和认识论问题。关于心灵的形而上学问题包括了,心灵是否是非物质的实体,心理现象如何适合因果顺序。或许,心灵哲学中最为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是关于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心身问题。关于心灵的认识论问题包括了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关于不同于我们自身的心灵的知识,我们是否拥有对我们自身心灵的特别的获取知识的专有方式。
把心灵哲学简单地归结为是关于心灵的哲学问题,这并不非常准确,因为对心理学哲学也可以这样说。不同的哲学家对这两个部分在观点上各有不同。但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区别:如果我们说心灵哲学关心的是我们关于心理现象的日常生活观念,那么,心理学哲学关心的问题则是出自对心理现象的科学研究(这种现象就出现在大学的实验心理学系)。当然,这个区分是人为的,因为科学心理学也大量地运用了我们思考心灵的日常方式,反过来,日常的观念也毫无疑问地受到了心理学发现的影响。不过,这个区分还是足够的。
我们日常的心理问题观念使用的是思想的概念,更为专门地说就是指欲望、意向、推论和计划等,以及出于理性而行动的概念。日常的框架也包括了经验观念,更为专门的是知觉、感觉、情绪和意识。这些概念框架是以“常识心理学”为著名。心灵哲学则是要分析,阐明和联结常识心理学的概念,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日常用来描述和解释思想、经验以及他人的和我们自己行动的方式。
如前所述,心灵哲学涵盖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又与心理学哲学有所交叉。它还与哲学的许多其他领域有着密切联系,包括了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在当代哲学中,它与语言哲学的联系更为凸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语言哲学占据了核心地位,被看作是处理最为广泛的传统哲学问题的方式。但对语言哲学中核心概念的研究(语言意义概念),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关于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的问题,在最近几十年里,心灵哲学逐渐取代了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大多数哲学系学生会发现,心灵哲学比语言哲学更容易接受,与语言哲学不同的是,心灵哲学可以得到很好的入门教材。最近几年各种文集的出版物一直不断增加,很容易搞到很便宜的大量关键文章。心灵哲学的教科书通常以心身问题为开端,讨论的是心灵与身体的关系,特别是心灵与大脑的关系。这里要强调的主要是形而上学问题。近代关于心灵的形而上学主要是唯物主义的,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因为难以理解的是,心理状态在整个物质世界中如何能够具有自身明显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