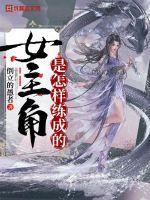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历史与现状(上下册) > 哲学主题导引(第2页)
哲学主题导引(第2页)
心理状态的典型例子是信念和感觉。每一种心理状态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信念的情况中,我们的问题是要理解信念如何能够是关于事物的信念。在感觉的情况中,难处在于触及了它们的现象学。
笛卡儿的世界观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实体:占据了空间的实体(物质)和思想的实体(心灵)。当笛卡儿坐在火炉旁冥思苦想,他的身体占据了火炉前的空间,他的心灵则享受着思想(“我在这里,依火炉而坐,身着冬天的外套……”)。根据这种世界观,心灵如何拥有关于思想的信念这个问题,可以被看作是毫无意义的,就像是身体如何能够在空间中延展这个问题一样毫无意义。关于事物的思想正是心灵之功能,如同在空间中延展正是身体之功能。但是,一旦我们认为心灵是物质世界组织中的一部分,我们就会疑问,占据空间的实体如何也能够成为思想的居所。如何能够产生这样的想法,某些(并非全部)物质事物中的某个(并非全部)物质行为是关于世界中的其他事物的,比如火炉,或外套?物质事物的某个行为(比如感觉)如何能够具有主观的现象特征,这个问题更为严重。我们可以承认,物质的大脑在某种意义上对意识的产生负有责任。但神经末段的活动如何能够产生现象学,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却是完全神秘的。
某些神经活动是(至少构成或组合了)信念和感觉。因此,我们大脑中发生的一切就有了这样的一些属性,比如作为关于火炉的信念,或者是作为温暖的感觉,以及拥有了神经生理学的、化学的,并最终是物理学的属性。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观念,后面这些属性(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的物质属性)在因果序列中发挥着作用。它们使得事物的表现方式产生了差异。我们日常生活的常识心理学框架也使得心理属性产生了差异。正是因为我拥有关于某物的具体信念,或者拥有某个特殊的感觉,我才以某种方式行动,才以某种方式移动我的身体,由此就影响到了事件的进程。但是有一些哲学论证似乎在危害着这样的看法,即物质世界的某些心理方面在决定历史进程中如何继续发挥着一种因果作用。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领域,需要更多的研究。
以上可以说代表了心灵哲学中的标准内容和核心内容。但仍然有一些东西被遗漏了,完全没有提及。要把这些遗漏的东西全部开列出来就太长了,这里可以提到的是三个重要的话题。
这里很少谈及的是关于心灵的认识论问题。这分作两个部分。一方面,有些问题是关于心理过程(如知觉、记忆和学习)能够使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另一方面,有些问题是关于我们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过程本身的知识。第二组又分为关于我们对其他人心灵知识的问题和关于我们知道自己心灵(显然是专门的)方式的问题。
这里对常识心理学的性质也谈论得不多。我们有能力去描述、解释和预测人们的经验、思考和行为等。我们从事的实践活动依赖于我们的常识心理学观念。但是,当我们反思我们的常识心理学实践时,这种能力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东西却并不是立即显现出来的。许多哲学家认为,我们的能力是基于关于经验、信念和行为的常识经验理论,关于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其典型的结果是什么,但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有许多理由会支持另一种观点,即认为说我们理解他人基本上取决于在想象中认同于他们的能力。
关于常识心理学性质的哲学争论是与发展心理学中关于儿童学会理解他人心理活动的方式的争论并驾齐驱的。无论是在哲学中还是在心理学中,大多数工作都是开始于对情绪的研究。当我们把心灵哲学与伦理学和美学中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个话题就至关重要了。
六、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
以古代哲学著称的西方思想阶段大致经历了一千年的历史,从大约公元前600年一直到中世纪早期。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两个伟大人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以前如苏格拉底等著名的前辈们。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是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用希腊语写作。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种古代文化的哲学呢?因为正是在希腊世界中,西方传统所理解的整个哲学才获得了自己的形式。伯纳德·威廉姆斯写道:“希腊对西方哲学的遗产就是西方哲学。……希腊人创造了哲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形而上学、逻辑学、语言哲学、知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及……艺术哲学。他们不仅开始了这些领域的探究,而且不断区分了应当被看作是这些领域中许多最为基本的问题。此外,带来这些发展的人只有两个,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被看作是最大的哲学天才和最高的哲学成就,正是这些使得哲学得以闻名于世,并在西方世界得以研究。”
于是,在研究这些早期思想家时,我们发现了哲学从何而来;但我们也发现了哲学以一种更为全面的方式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希腊思想家们发明了我们的主题,首次提出了最为深远的问题。他们的著述具有一种方向性和新鲜感,后来的哲学从来没有完全重新感受过。令人兴奋的是要重新追溯这些步履,发现我们可以与古代的哲学家们进行交流——我们仍然在做相同的事情。
不过,古希腊的某些思维方式可以表现为一种遥远的时代。在我们看来很是明显的东西,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可能从来就没有被思考过,而在他们看来明显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可能晦涩不明。在我们可以研究他们的哲学之前,我们必须试图形成一幅关于他们的概念和论证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图像。验证柏拉图的某个论证的说服力与试图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在这两者之间要达成一个平衡:我们是要从哲学上去思考,但我们也要采用历史的观点。学习古代哲学的学生有时会发现很难达到这种平衡。正是在古代思想家那里看到的对历史久远性和哲学深刻性之间的混合,才使得他们成为独一无二的永久研究对象。
七、近代哲学是理性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的较量
哲学史上的“近代”时期通常被看作开始于17世纪,以培根的《新工具》(1620)和笛卡儿的《论方法》(1637)为代表。培根和笛卡儿都不是孤立的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处处都受到了他们的前辈和同代人的影响。不过,把他们看作是开启了近代哲学的人却不是随意的,因为正是他们摧毁了中世纪早期以来在哲学中一直被视为常识的那些假定、方法和语言。
人们通常按照康德的做法,把17世纪的哲学家和18世纪的哲学家分作“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笛卡儿是第一类的代表,而培根则是第二类的代表。这种区分经常受到质疑,有些作者完全放弃了这种区分。然而,它在描绘这个领域的最初版图的时候还是很有用处的,它也被毁誉参半地纳入到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之中。因此,通常的方式是把近代哲学的历史区分为三个部分:经验主义者(培根、洛克、巴克莱、休谟)、理性主义者(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康德,由于康德有意识地反对这两种对立的传统,所以应当把他单独地考虑。大致地说,经验主义者相信,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并由感觉经验加以证明;理性主义者则认为,只有通过理性的思想才能获得知识;而康德认为,知识包含了一种综合,感觉和思想的能力都在综合中得到了统一。
哲学史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构成了对论证的探索和批评,从这些论证的历史背景中得到了提升,并对这些论证的有效性进行断定。观念能够得到研究,正是由于它们提出了我们至今仍然关心的问题。哲学史因此不同于观念史,后者属于历史的一个分支。观念史学家关心的是观念的起源和影响;但他可能对观念的真或有效性并不关心。大多数人都无法清晰地或连贯地思考;因而荒谬的想法通常会比严肃的论证产生更大的历史作用,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考虑观念历史的前景。但生命是短暂的,哲学则是险峻的;因此哲学史上研究的只有主要的思想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是考虑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康德,而忽略了他们的许多耀眼的同代人,包括马勒布朗士、帕斯卡、沃尔夫和鲍嘉通,这里只提这四个人。
哲学史与观念史的区别并非我这里所说的那样清晰明了。许多作者质疑你可以从一个观念的历史背景中获取一个观念,而不把它变为其他的东西。例如,他们认为,你可以理解一个论证,只是通过研究形成了这个论证的争论以及用于表达这个论证的语词的当代意义。这样的作者更多地注意的是历史的细节,追溯影响的踪迹。相反,其他人则抓住了伟大的先哲,赋予他们生命,不留情面地拷问他们,仿佛他们就是同代人一样。后面这种人对学生来说更为有用;但第一种人也不能轻视,因为他们是这个学科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开端。
在近代早期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中,有三个特别突出,即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他们提出了广泛的哲学问题,但这里主要关注他们对知识论的贡献。他们虽然都共同声称接受经验主义,但其中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用一个统一的标签“英国经验主义者”就应当不会带来模糊。他们的重要性是巨大的,当代关于知识论的争论以及相关的探索都来源于他们的工作。
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认为,偶然知识的来源和验证是经验。“经验”主要是指感觉经验,就是说运用五官,以及必要时使用类似显微镜和望远镜这样的工具。但这也包括经验者的心灵内容和活动的内省意识。以通常用于哲学史导论中的一种多少有些简单的方式来说,经验主义是与理性主义对立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主张认为,知识的主要路径是理智而不是感觉。理性主义典型地被刻画为这样一种观点:知识的专门对象是内在永恒的真理,但凡不属于这种真理的东西都无法成为知识的恰当目标,而不过是一些意见或信念的目标。经验无法使我们得到这种真理,因为经验所能给我们提供的大多是关于事物在历史的某一点上如何偶然发生于我们这个宇宙中的多少或然的信念。要掌握这种无条件的真理,我们就必须超越经验的限度,或者我们可以拥有在经验之外的来源。所以,只有理性的运作或者是先天的禀赋或者是两者才能使我们拥有知识。
理性主义的知识范式据称是形式演绎系统,比如几何学或逻辑学,而出自第一原理、自明真理或定义的设计,则导致了全部确定的知识。相反,经验主义者认为,知识无法来自扶手椅上的沉思,而只能来自于行动和观察。运用我们的感官(以及扩展其范围的工具),就可以告知我们偶然的事实。他们认为,把形式演绎系统看作是知识的范式完全是个错误,因为它们完全不是相同意义上的知识,而仅仅是“分析的”,就是说,它们只有因为用于表达它们的那些语词的定义才是真的。一个例子就是同义反复陈述。同义语是分析陈述的一个特例,它们与其他分析陈述的不同就因为它们非常明显。“单身汉是没有结婚的男人”就是一个分析陈述,而“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是一个男人”则在同义反复的意义上是一个分析陈述。在这两种情况中,分析性就在于(大致地表达传统的观点是),对主词所要断定的东西已经包含在了主词之中。重要的是要看到,是否真的存在分析性这样的特征,还存在争议。
经验主义的知识范式是自然科学。因此观察和实验就构成了知识的两个来源,也是使知识合法化的方式。经验主义者把成功的科学实践看作是对自己观点的证明。
对这两个思想流派的刻画忽略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理性主义者是如何论述知觉的,经验主义者又是如何谈论先天知识的。以下考虑的三个哲学家并非完全符合经验主义者的特定图像。但他们都同意这个图像,因此都相互承认了经验的根本作用。
人们会以为,经验主义的观点会导致一些有问题的后果。一个是,只有在经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自身赋予概念时,概念才会有内容,或者说,语言表达式才会有意义。经验主义者声称,背离了经验所能合法化的东西,就会导致自身是空虚的或无意义的(这提出了两种经验主义:一个是说经验是概念的来源,另一个则说经验是概念合法性的根据。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这个区分在这里并不需要)。人们可以立即看到一个难题:如果人们在物理世界方面接受了“实在论”,这在哲学上就是认为(再次概括地说一下),世界的存在不依赖于经验,那么人们似乎就会与经验主义相冲突,这就无法有意义地谈论超越经验的东西。这并非是第一位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所能解决的张力,而他的两个后继者则试图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八、伦理与道德的区分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同利益关系
道德哲学是对关乎人类的某些价值的哲学反思性研究。伦理价值的一个意义在于告知人们的生活,直接决定应当做什么,以及他们对人们和行动的评论和判断,包括对他们自己的。人们试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按照这样的价值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们认为(虽然并不是十分清楚地),某种生活比其他的生活更值得过,试图培养自己的孩子共有自己的观点,或者提出一种他们同样希望能够得到尊重的观点。除非生活令人绝望,大多数人还是会对他们的行为接受道德的限制,比如,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大多数时间里)拒绝撒谎或骗人,(几乎在所有的时间里)拒绝杀人或伤人。由此,道德哲学试图理解某些行动的理由。对于行动的决定(我应当做什么?)并不是道德哲学的唯一考虑,但却是道德哲学兴趣的重要焦点,其他的考虑还有,我们以道德的或伦理的方式对自身和他人所作的各种承诺、断定或判断。
“道德哲学”或“伦理学”这两个名称并没有什么不同,但“道德的”和“伦理的”这两个词却多少有些不同的共鸣。“伦理的”(来自希腊文,意谓“个性特征”)承载更为宽泛的观念,包括了关心各种不同种类生活和行动的价值;“道德的”(来自拉丁文,意谓“社会习俗”)则把其兴趣限制于规则和义务,以及与它们更为密切相关的经验和考虑。“道德的”通常是被用于(虽然并非必须如此)这样的方式,即要对某个考虑或感情是否符合某个道德这样的情况作出一个重要的区分:譬如,悔恨可以被严格地对比于其他形式的遗憾,作为一种恰当的道德反应;而与机智或性感这种属性相比,个性特征是否严格地具有道德价值,这可以成为一种焦虑。日常经验中存在这种区分的一定基础,但不能把它们看得太重:理智、敏感性、移情想象、一定的韧性,这些都可以与道德生活相关,但没有作为专门的“道德”属性。对这种区分的过分夸张似乎是道德价值理论的产物,特别是过分强调了意志的道德理论。
“伦理的”和“道德的”是与其他种类的考虑相对立的,虽然这些界限常常是(也很重要)模糊的。一个重要的对立面就是自私的考虑,当然,虽然这个对立可以是在不同的地方,这取决于“自我”的意义。我的家庭要求可以说代表了对我的伦理要求,由此反对我纯粹的私人利益;但面对更为广泛的社会要求或集团要求,我的家庭利益本身则可能被看作是我们的私人利益问题。在不同的程度上,伦理的考虑可以比对审美的、经济的、政治的或宗教的考虑。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各种考虑必然都会相互冲突或牵扯向不同的方向,但只有涉及的各种理性、情感或利益才是典型地不同的。
在更为广泛的程度上,道德哲学与哲学的其他领域相比,更难以严格地区分于其他的哲学研究,或哲学之外的学科。道德体验涉及了许多关于个人生活及其与他人关系的更为深层的思想和情感,而同时,道德规则和期望则构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它控制着社会并构成了每个公民之间的关系。对道德哲学的兴趣更好地维系着与其他学科的密切联系,比如,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哲学心理学,以及与其他各部分的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持续地使道德哲学变成抽象的和非实在的倾向,则是需要由想象的文学和历史相互抵消的,这不断地提醒人们,现实生活在道德上既是复杂的,(可以注意到的是,有时还是富有成效的),也是对道德的抵制。目前的研究是以最强的理论形式展现了这个主题,但对这个研究的阅读则应当认识到,道德哲学必须从其与现实经验的关系中最终获得自身的利益,这些经验并非全都是哲学的或道德的。
九、美学是对审美体验和判断性质的统一性追求
美学可以区分为审美哲学和艺术哲学。审美哲学关心的是一般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判断,以往关注的是“美”这个概念。当代分析哲学中的美学主要关注的是艺术哲学,涵盖了与形而上学、伦理学、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等话题相互交叉的广泛的问题领域。
哲学美学正如传统上一直被认为的那样,被看作是基于两个主要假定。阐明了这两个假定也就得到了它的主要目的。
第一个假定是认为,对艺术和自然之美的鉴赏存在一种共同的明显体验形式,这典型地具有一种令人愉悦而又产生沉思的特征,关涉到从现实生活关注的解脱感,并使得我们以一种完全是语词的方式,比如优雅的、美丽的、令人启发的等等,去描述美的对象,包括艺术作品、自然的景致和对象。哲学就是指这种体验,以及导致我们作出的“审美”判断。
第二个假定是认为,艺术具有一种本质,或者是某种内在统一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常识性的观点。虽然各种艺术形式(音乐、文学、绘画等)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毫不相似,但我们把它们都应用于艺术概念,我们并没有把这看作是一种随意的分类。因而,哲学美学的传统目标一直被看作是对审美体验和审美判断性质以及艺术统一的论述。
尽管对人类生活的审美问题随处可见,审美体验和审美判断在反思上最终可能是神秘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什么可以解释审美体验的具体特征?判断一个对象是美的,如同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个判断如何能够报道一个关于对象的事实以及表达主体的感情?如果似乎没有解决争端的方法,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争论对象的审美价值呢?艺术的概念在反思中体现出同样缺乏哲学的清晰性。是什么使得一个对象成为艺术作品?正如通常认为的那样,艺术如何能够使我们接触到艺术家的心灵?音乐如何能够拥有意义,表达人类的情感?当评论家对艺术作品的意义有分歧的时候我们又会怎样想?我们为什么要对艺术赋予一种意义,而我们却不会对体育和美食赋予这种意义?如此等等。
围绕一般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判断性质的问题,需要集中关注的是两位历史人物的著作,即休谟和康德。他们对艺术的哲学理解涉及至关重要的概念,诸如表征和表现。这些概念在逻辑上正是关系到艺术作品的基本方面,如今的分析哲学也密切关注这些概念。而美学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是要描述艺术的性质和价值,关注到美学在伟大的哲学体系中的位置。
总体框架
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