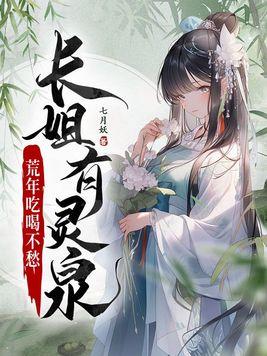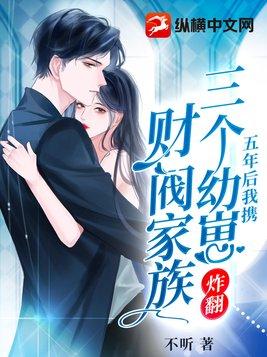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叩天阙 > 掀翻棋盘(第1页)
掀翻棋盘(第1页)
腊月将尽,北境的风雪酷烈如刀,官道断绝,驿马难行。然而一队打着兵部旗号的人马,却奇迹般地出现在云中城北百里外的一处驿站。为首的官轿帘幕低垂,仪仗规整,一切符合钦差规制。
可真正的兵部左侍中周霖,此刻却是一身青衿,带着两名扮作书童的健仆,踏着没膝的积雪,艰难行在云中城外的乡间小道上——她生性多疑,不信边关奏报,更不信秦王“病重”之言,故而行此暗度陈仓之计,欲亲眼看看这北境,究竟是谁家天下。
首先撞入眼帘的,是那高耸得令人心悸的城墙。黑石垒砌,雄堞如齿,在风雪中沉默矗立,远比她见过的任何边城都要巍峨坚固。城头玄旗招展,甲士巡弋的身影在风雪中若隐若现,那股肃杀之气,隔得老远便能感受到。
更令她心惊的是沿途所见的一座座巨型仓廪。即便是在这荒僻村落旁,亦能看到新修的仓房,覆雪之下,犹能窥其规模,绝非寻常州县可比。时有押运粮草的队伍在清扫出的道路上沉默前行,车辙深重,井然有序。
甚至就连官道,都比上京的官道还要平坦宽敞几分。
行至一处村落,周霖假意歇脚,向一位正在清扫屋顶积雪的老农打听:“老人家,敢问此地……可是云中辖下?我看这仓廪充盈,城墙高阔,不知赋税……可还沉重?”她刻意模仿着游学士子的口吻。
那老农停下活计,用粗糙的手抹了把脸上的雪水,咧开嘴,露出被寒风刻满皱纹的笑容:“后生是外地来的吧?俺们这旮沓,以前苦啊,世家姥姥们的地,租子重得能压死人。自打大王来了,不一样喽!”
她指向远处的仓廪:“那是大王的义仓!年年丰收,大王就让人建仓存粮,遇到灾年或是青黄不接,就借给俺们这些泥腿子,利息?那是什么玩意儿?大王说,北境百姓活命最重要!”
老农越说越激动,放下扫帚,比划着:“大王还常来哩!不带多少随从,就骑着那匹大黑马,到田埂上,跟俺们唠嗑,问收成,问娃儿能不能吃饱穿暖。俺家那小崽子前年病得快死了,就是大王碰巧路过,让随行的官人给救回来的!”她眼眶有些发红,“这恩情,俺们记一辈子!”
周霖心中已是波涛汹涌,强作镇定问:“哦?秦王竟如此亲民?只是,她毕竟是天家贵胄,如此收买人心,难道不怕朝廷……”
“朝廷?”老农愣了一下,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摆摆手,“朝廷在哪儿俺不知道,俺就知道,是秦王大王让俺们有田种,有粮吃,娃儿能活命!后生,俺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她压低了声音,却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虔诚,“这北境的天,是秦王大王撑着的!要是大王需要,俺这条老命,随时可以拿去!不光是俺,你问问这十里八乡,谁家不念大王的好?谁不愿为大王去死?”
周霖悚然一惊,一股寒意自脚底窜上脊梁,她看着老农那浑浊却无比坚定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丝毫作伪,只有近乎信仰的赤诚。这已非简单的民心可用!
出身世家的周霖从前从未想过这些泥腿子会颠覆朝廷,她认为“礼不下庶人”,更认为这些人不懂“士为知己者死”,但听完老农这些话,她恍然意识到——以云中城为中心的北境三十五城里,有多少受了秦王恩惠的百姓,她就有多少愿意为她赴死的死士!
高平陵政变只需三千兵马,唐隆政变只需两百兵马,可秦王——她拥有为她赴死的兵马何止三万!
她不敢再多问,匆匆告辞。一路行去,又“偶遇”几名樵妇、货娘,言辞或有差异,但对秦王的感佩与誓死效忠之心,如出一辙。整个北境,仿佛一张无形的大网,而织网之人,便是那位称病拖延回京的秦王。
周霖遍体生寒。
---
三日后,周霖与自己的仪仗队在云中城外的驿站会合。她换回官袍,一扫连日暗访的惊悸,重新端起了朝廷大员的倨傲。她确信自己掌握了秦王的把柄——高筑墙,广积粮,收买明心,这分明就是谋反的前兆!
秦王府正厅,炭火依旧温暖。
周霖手持圣旨,立于厅中,目光锐利地扫过略显“疲惫”的嬴长风,以及她身后肃立的云书、崔归、尉迟澜、凌城等人。她不再虚与委蛇,开门见山,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秦王殿下,本官奉陛下之命,宣慰北境,协理军务。如今边情紧急,军机瞬息万变,为免贻误战机,本官决定,即日起,北境一切军务,皆由本官代行裁决!兵符印信,一应文书,请殿下即刻移交!”
她顿了顿,语气更冷,意有所指:“此外,本官沿途所见所闻,颇多不合规制之处。望殿下好自为之,莫要自误!若殿下执意不改,本官只好奏请天子,以正名法典!”
厅内一片寂静。
周霖预想中的惊慌、辩解、推诿并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