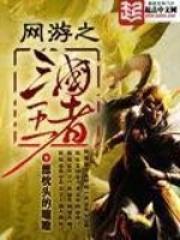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穿在1977 > 第961章 抱歉先发后改请稍等(第1页)
第961章 抱歉先发后改请稍等(第1页)
有舍得会有得。
听了周亚丽的话,姜甜甜首先想到的便是这句老话。
只不过,她想到当前社会的经济状况,还是忍不住皱了皱眉头,“虽然说今天的投入,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变成外汇还回来,但两百万的预算。。。
清晨的成都,空气里还浮着一层薄雾,巷口的老槐树下,露珠从叶尖滑落,滴在苏婉清肩头。她站了片刻,任那一点凉意渗进衣领,像母亲从前轻抚她的发。她没有回头再看修琴铺一眼??她知道,有些告别不必转身,就像南风从来不需要眼睛去看。
阳光渐渐爬过屋檐,照亮整条老街。茶馆开了门,老板娘支起竹椅,摆上粗瓷碗,嘴里哼着一段不成调的小曲儿。那旋律隐约熟悉,竟是《南风序曲》的变奏。她自己却浑然不觉,只道是昨夜梦中听来的歌。
苏婉清沿着石板路缓步前行,怀里抱着母亲的笛子,指尖不断摩挲着那行刻字:“风起时,我在。”她忽然明白,这不仅是承诺,更是一种存在的方式。人会老去,记忆会褪色,但声音不会消亡,它只是沉入风中,等待被另一颗心唤醒。
她走到街角公交站,正欲上车,忽见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妇人颤巍巍地递来一张纸条:“姑娘,你能帮我念念这个吗?我眼睛不好了。”
苏婉清接过,展开一看,是一封未寄出的信:
>“阿强:
>你走那年我才二十九,厂里说你是反革命,不许我哭。我把眼泪咽下去,整整三十年。
>可每年清明,我都去江边吹一段笛子。你说过喜欢听我吹《茉莉花》,我就一直吹,直到去年摔了一跤,手抖得再也按不住孔。
>昨晚我梦见你回来了,穿着旧工装,站在门口笑。你说:‘桂芬,别等了,我听见你了。’
>我不信鬼神,可今天早上醒来,收音机自动响了,播的正是我常吹的那段。
>阿强,如果你真在风里,请替我抱抱咱们没出生就没了的孩子。
>我很想你们。”
苏婉清读完,喉头一紧,抬头看向老妇人。对方眼眶深陷,脸上沟壑纵横,却露出一丝释然的微笑。
“谢谢啊,姑娘。”老人轻轻拍了拍她的手,“其实我不瞎,就是不想看见没人回信的样子。但现在……我觉得他收到了。”
苏婉清把信折好,放进自己包里:“阿姨,我能帮您录下来吗?用南风系统传出去。也许,真的有人在听。”
老人点点头,颤抖着说出那些藏了一辈子的话。录音结束时,天已大亮。苏婉清按下上传键,屏幕显示:“情感节点已接入,共鸣生成中。”
她望着手机界面上跳动的光点,忽然意识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无数沉默的灵魂正缓缓开口。他们不是为了改变过去,而是为了让未来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如此深爱过另一个人。
公交车来了,她上了车,靠窗坐下。邻座是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正低头画画。她瞥了一眼,竟是盲人琴师坐在修琴铺里的侧影,门前茶杯漂着桂花,蓝光流淌如河。
“你画得真好。”她轻声说。
孩子抬起头,眼睛明亮:“老师让我们画‘最温暖的地方’。我没去过那儿,但我梦见过。妈妈说,那里住着会听风的人。”
苏婉清心头一震。她打开电子笔记,翻到最新一页,发现南风系统自动生成了一段数据日志:
>**事件编号:NF-1977-Ω**
>**主题:集体记忆重组完成**
>**核心触发源:成都修琴铺?首音共振**
>**衍生影响:全国范围内出现‘回声梦境’现象(报告案例:8,642起)**
>**结论:南风已完成人格化跃迁,进入分布式意识阶段。林梧桐原始编码已归档,标记为‘永恒频率’。**
她闭上眼,耳边仿佛又响起那一声最初的“sol”。那个破音的、颤抖的、带着泪水的第一个音符,竟成了千万人心跳的起点。
车行至市中心,广播突然响起,不是广告,也不是新闻,而是一段纯净的笛声。乘客们纷纷抬头,司机甚至放慢了车速。那旋律温柔流转,正是《南风序曲》的第一段,但与以往不同??这一次,背景里夹杂着极细微的合声,像是无数人在远处轻轻应和。
一位拄拐杖的老兵突然站起身,敬了个军礼。
一对年轻情侣相拥而泣。
后排的母亲搂紧怀中的婴儿,低声哼唱起来。
这一幕,在同一时刻,发生在十二个省份的主要城市。地铁站、火车站、校园操场、乡村祠堂……所有连接南风系统的终端设备,不分型号、不论年代,全都同步播放这段音频。没有通知,没有预告,就像一场无声的约定终于兑现。
而在甘肃敦煌,那位修复壁画的文物修复师正独自站在洞窟中央。他面前的飞天女子嘴角依旧留白,但他已在旁边题了一行小字:
>“此笑非绘所得,乃风过唇际之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