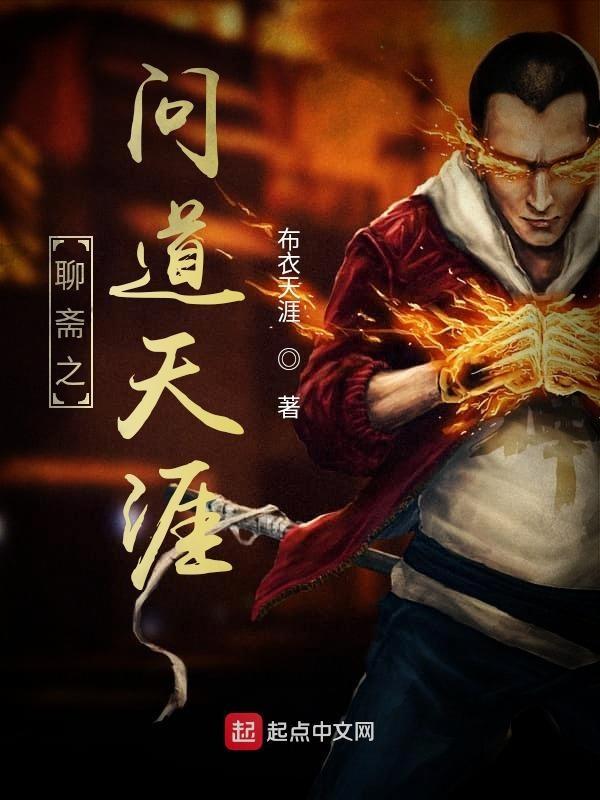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人间有剑 > 第四百五十五章 相见于雨中(第1页)
第四百五十五章 相见于雨中(第1页)
仙官看着断气的长草道人,面无表情。
世间万物,所作所为,自有内因,那长草道人那般痛恨道门弟子,其中缘由若是真说出来,或许对他来说,如此行事,本就是无错。
但仙官身为大真人弟子,世间道门弟子是同道,站在此处,那长草道人便要杀,杀了他,对那些道门同道,有交代,对天宫来说,方能使威望不堕。
所以他来此处,只为杀人,不为细究对错。
有时候对错很重要,但有时候,对错又很没有意义。
仙官收起那狐狸尸身,看了一眼。。。。。。
夜深了,祁连山的风再次穿过知语堂的窗缝,吹动那幅《言剑》复刻版的一角。纸面轻轻抖动,像有谁在暗处低语。青年坐在桌前,手中握着云知留下的旧钢笔,墨水瓶里的幽蓝光芒微微荡漾,仿佛映照出无数未曾说出的句子。
他刚从一场漫长的梦中醒来。梦里,他站在一条无尽长廊上,两侧是密密麻麻的档案柜,柜门自动开启,每扇门后都坐着一个人??陈默在抄写被删节的社论,赵立新用铅笔在牢房墙上刻字,周振国点燃一叠稿纸,火光照亮他决绝的脸,李文秀蹲在边境小屋,对着录音机轻声讲述一个村庄的饥荒史……而最深处那扇门缓缓打开,走出一位穿灰布衣的女子,眉目清冷,手里提着一盏油灯。她没说话,只是将灯递向他。
他伸手去接,却惊醒过来。
此刻窗外月色如洗,梧桐树影斑驳地洒在地面,像一页页散落的手稿。他低头看桌上的留言簿,发现不知何时,竟多了一行陌生的字迹,墨色淡得几乎要看不清:
>“她说:别让光熄了。”
心猛地一缩。这不是他的笔迹,也不是近来任何访客所留。他立刻翻查监控录像,却发现昨夜十一点十七分至十二点零三分之间,所有画面皆为一片雪白噪点,唯独音频记录下一段极轻的脚步声,以及一声几乎不可闻的叹息。
他拨通老太太的电话,铃响了很久才接通。
“您看到了吗?”他问。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看到了。”她的声音沙哑,“那是‘守灯者’的暗语格式??只有我们五人知道的书写方式。不是模仿,是真迹。”
“可您不是说,其他人都……”
“我以为都走了。”老太太打断他,语气忽然变得遥远,“但也许,有些人从未真正离开。他们只是沉入更深的地下,像根系藏于泥土,等某一刻春雷响起,便再度抽枝。”
青年怔住。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自从李文秀到来之后,知语堂的电力系统开始出现异常波动。太阳能板读数正常,蓄电池也满格,可每到午夜,灯光总会忽明忽暗,像是某种信号在试图传递。更奇怪的是,卫星通讯设备每次启动,都会自动跳转到一个未登记的频段,接收一段杂音般的波形,破译后竟是断续的文字:
>**……桥未断……
>灯仍在烧……
>有人还在听……**
他把这段数据发给周念,请她用《灰幕》项目的解码算法处理。三小时后,她回信附上一份重构文本,内容令人脊背发凉:
那是一份1984年夏秋之际的加密广播日志,源自一台隐藏在青海湖畔废弃气象站的短波发射器。操作者使用代号“回声0号”,每日凌晨三点准时播送十分钟内容,持续整整四十三天。播送内容包括《言社宣言》残篇、赵立新早期调查笔记摘要、李文秀逃亡途中写下的诗,以及一段反复播放的童声朗读:“**言即灯火,说者不孤。**”
最关键的是,在最后一次广播结尾,传来一阵剧烈干扰,随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冷静而清晰:
>“若你听见此声,请回应。我们在等火种归来。”
“这不可能。”青年喃喃道,“1984年,云知已经失踪两年了!”
周念回复:【技术分析显示信号真实存在,且发射源经三角定位确认位于东经99。8°,北纬36。7°??正是当年‘言社’最后据点所在地。更诡异的是,该频率至今仍周期性激活,最近一次出现在三天前,也就是李文秀抵达当晚。】
青年猛地抬头看向窗外。远处雪山轮廓在月光下泛着银辉,宛如一道静默的碑林。他忽然想起李文秀说过一句话:“我在逃亡路上学会了一件事:真正的秘密,不会写在纸上,而是藏在声音里。”
他冲进地下室,翻找云知遗物箱。在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的夹层中,他找到了一张薄如蝉翼的磁带,标签上写着三个小字:“回声桥”。
他颤抖着手将磁带放入老式录音机。机器嗡鸣启动,扬声器传出沙沙的底噪,接着,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女声缓缓响起:
>“我是云知。如果这段录音还能被人听到,说明‘桥’还没有彻底坍塌。1982年冬,我被捕前三十六小时,完成了最后一项计划:我们将所有重要资料转化为声波编码,埋入全国三十座图书馆的馆藏唱片之中。这些唱片外表普通,实则经过特殊调制,唯有用特定速度反向播放,并配合摩斯密码对照表,才能提取信息。它们分布在兰州、昆明、成都、西安……每一处都是‘言社’曾经活跃过的城市。”
>
>停顿片刻,她的声音更低了些。
>
>“我不是被捕,是我选择了被捕。因为只有这样,追查才会集中在我的身上,给你们争取时间。我对不起你们每一个人,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重新拼凑起这张网。当第五个名字归位时,‘回声桥’就会重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