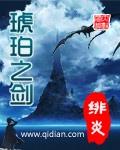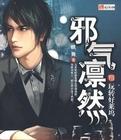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华娱:重生了,还逼我做渣男啊 > 第六百二十四章 死都不会接(第1页)
第六百二十四章 死都不会接(第1页)
一张会议桌上,一台三角形状会议电话机正放置在中央,绿色的指示灯正在亮着。
扬声器里,一个女人的声音正在说着:“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乔治,你们应该明白,你们提出的报价是我们绝对无法接受的。诺兰导。。。
广西大石山区的清晨,总是从一声咳嗽开始。
天还没亮透,山雾如纱般缠绕在陡峭的岩壁之间,村道上湿漉漉的青石板泛着幽光。一栋低矮的土屋静静伏在半坡,屋顶盖着陈旧的瓦片,檐角挂着几串风干的玉米。屋里,一盏煤油灯早已点亮,昏黄的光晕透过糊了报纸的窗棂,在地上投出一个摇晃的方块。
床边坐着一位中年女人,名叫阿英。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用一根木簪随意挽起,手里握着一支铅笔,面前摊开一本边缘卷曲的练习册。她的目光紧紧盯着床上那个瘦削的身影??父亲秦绍文,正靠在叠了三层的枕头之上,胸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每呼出一口气,喉咙里便滚过一阵沉闷的咳声。
“今天……讲《岳阳楼记》。”他声音微弱,却字字清晰,“先背一遍。”
阿英点头,放下笔,轻声诵读:“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她背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老人抬起枯瘦的手,轻轻摆了摆。
“停。”他说,“这句,要慢一点念。让学生去想??什么叫‘忧’?不是愁眉苦脸,是心里装着别人。”
阿英记下这句话,写在教案旁的空白处,标注:“重点讲解‘忧乐观’”。
这是他们二十年来的日常。秦绍文曾是县中学最负盛名的语文教师,三十年教龄,带出过无数考上大学的孩子。五十八岁那年突发脑溢血,抢救回来后全身瘫痪,只能卧床,连翻身都需要人协助。医生断言他活不过两年。
但他活到了第二十一年。
因为学生还在等他讲课。
起初只是几个老同事带着学生上门求教,后来消息传开,越来越多偏远村寨的孩子托人送来作业本,请“秦老师批改”。有人提议录音,可老人家坚持口述授课,由女儿逐字记录、整理成讲义,再通过志愿者邮寄或微信发送给各地师生。
久而久之,这套手写教案竟累积超过三百课时,涵盖初高中全部古文篇目,甚至包括高考作文技法指导。有些孩子拿着这些讲义考上了重点高中,还有人专门写信来感谢:“秦老师没教过我一天面授课,但我把他当成真正的启蒙恩师。”
陈诺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是在《心光》纪录片获奖后的分享会上。一位来自广西河池的支教老师含泪讲述:“我们那儿有个孩子,家里穷得点不起电灯,就借着灶火的光看秦老师的讲义。他说,那是他人生第一次明白,读书不只是为了逃出大山,而是为了不忘记大山。”
那一刻,陈诺的心被狠狠撞了一下。
三个月后,他带着摄制组踏入这片被称为“地球裂缝”的喀斯特地貌区。山路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行,两侧是深不见底的沟壑,脚下碎石常因雨水松动滚落崖底。老周一边走一边嘟囔:“上次在怒江差点摔死,这次怕是要掉进地缝里。”
可当他们终于见到秦绍文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老人躺在一张吱呀作响的木床上,脖颈以下毫无知觉,右手蜷缩变形,左手勉强能抬至胸前。但他的眼睛依然明亮,像两簇未曾熄灭的炭火。听见脚步声,他转过头,嘴角缓缓扬起。
“来了?”他问,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安定感。
阿英坐在旁边翻译,将父亲的话转述出来:“他说,欢迎你们来。不过有个条件??不准拍他流泪的样子,也不准拍他痛苦的表情。‘我不是悲剧人物,只是一个还在工作的老师。’”
陈诺怔住,随即郑重点头。
拍摄从第二天清晨正式开始。
每天五点半,阿英准时起床烧水做饭,顺便检查父亲的身体状况。六点十分,她把床头的小黑板擦干净,准备好纸笔和录音设备。六点十五分,秦绍文睁眼,示意可以开始。
第一节课便是《岳阳楼记》精讲。
“范仲淹写这篇文章时,并未真正登上岳阳楼。”他缓缓说道,“他是听人描述,凭想象写的。可为什么千年后,我们仍觉得那景色真实无比?因为他心中有天下。”
阿英将这段话一字一句写下,又用红笔圈出关键词:“想象的力量”、“情感的真实高于物理的真实”。
陈诺悄悄把镜头推近,捕捉老人说话时面部肌肉的细微颤动。那种力量,不来自嗓音洪亮,而源于思想本身的重量。
中午,几个住在附近的留守儿童陆续到来,围坐在院子里的小桌旁,听阿英播放昨晚整理好的课程录音。孩子们认真记笔记,时不时举手提问,问题五花八门:
“秦老师,如果我没见过大海,也能写出关于海的文章吗?”